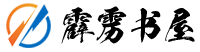满座上下当即鸦雀无声。
天子一怒, 那是要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即便是陛下这样的仁君,雷霆之怒下,也难保会不会留下桑知辛的脑袋。
一时间, 桑知辛与陛下面面相对着, 满座朝臣谁也不敢贸然起身请罪, 讷然不言的,像是一群缩脖子的鹌鹑。
方临渊也被惊得肩头一颤。
下一刻, 一只微凉的手轻轻落在了他的膝头,不动声色地按了一下。
方临渊转过头去,便见是赵璴在看着他。
“无事。”只见他低声说。
他们此时离御座有数丈之远, 这样小的声音陛下自然是听不见的。
……但赵璴的胆子是真大。
在座的官吏亲贵哪个不是大气都不敢出?唯独赵璴, 神色平淡中甚至隐带着轻蔑, 眉睫微抬, 淡漠地看向高台的方向。
就在这时,那边的桑知辛动了。
方临渊转头看去,便见他双手捧着酒杯, 端端正正地跪在了高台之下,酒杯举过头顶,深深地磕下头去。
“微臣明白陛下之言!”只听他高声说道。
在场众人皆是愣住, 谁也不知他此言是什么意思。
只听他接着说道。
“陛下跗骨之痛,是微臣为官不力之果!请陛下放心, 三日之内,臣定呈上肃清污吏之法, 荡清陛下朝野污秽!”
——
鸿佑帝没有言语, 摆了摆手, 让他退了下去。
方临渊清楚地看见, 桑知辛起身回席之时, 在场众人忌惮犹疑的神色和躲闪避忌的姿态。
他这一番话,显然是将自己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陛下对他仍没有回应,他却堂皇地将自己摆在了受审官吏们的对立面上,此时无论是他的僚属,还是高堂之上的皇帝,都不会再对他有分毫信任了。
片刻沉默之后,方临渊借着重新热闹起来的声音,转头问赵璴道:“他这是在断尾求生?”
只见赵璴笑了一声,说道:“你看出来了?”
“看是看出来了……”方临渊有些犹豫。“但是此举能成吗?他结党贪污的罪行已经闹到了皇上眼前,皇上怎么还会重用他?”
“我们送到宫中的罪证,也确实没有确凿是他的。”赵璴说。“只要没有证据能给他定罪,此举就仍是有用……”
说到这儿,他偏头看向桑知辛。
“虽胜算不大,不过是赌而已。”他说。“但反正已是死局一盘,没有退路,便随他挣扎了。”
听见这话,方临渊面上浮起了忧色。
“困兽之斗向来是最不可控的。”他说。“你有应对的办法吗?”
赵璴看着他,没有言语。
方临渊一时有些紧张。
“你莫非也没有算到他会有这一步?这就有些麻烦。圣心向来是最难揣测,若是他将兖州这样大的事都推了出去,那岂不是……”
他小声地自言自语着,却忽然,一道微凉的气息忽然凑近了他,在他毫无防备之际,轻飘飘地落在了他耳边。
“仍在我筹算之内。”是赵璴的声音,压得很轻。
方临渊浑身都僵了。
却听赵璴说道:“只是此事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而今身在宫中,总不好大庭广众地讲出来。”
他语气里懒洋洋的笑意飘在耳边,方临渊只觉自己是一座满是裂纹的石头。
僵硬得动弹不得,要是往旁边再搬一点,又会被捧得粉身碎骨。
“……原来如此。”
片刻,他硬邦邦地回应了一句,连人带着身下的红木座椅,朝着远离赵璴的方向挪了两下。
旁侧的赵璴微微一顿。
他目光里是方临渊面无表情、甚至显得有些冷峻的侧脸,而高束起的发冠让他的颈项与双耳没有半丝头发的遮挡,明晃晃地暴露在了烛火之下。
与那冰冷躲闪的神色不同,那儿却是柔软艳丽的一片绯红,像是蒸腾得起热气一般。
同样一副素来不大会伪装的面孔,却在他眼前冰火相触,当即将赵璴与人相与的薄弱经历全否定了,让他一时间都未能猜出个所以来。
赵璴眉眼微顿,继而不露痕迹地在那片绯红上停顿了片刻。
他虽不通情爱,却熟谙人性,知道神色可以作伪,可情欲的反应却不会。
更何况……
厌恶躲避某人,是不会令耳根泛红的。
这分明……该是气血上涌之情状。
——
两日之后,桑知辛便如当日所言,向鸿佑帝呈上了奏折。
这是在大朝会时公开呈奏的折子,里头竟林林总总罗列了整整二十一条,全是如何挟制地方官吏、如何控制仓廪粮草以及如何弹压地方豪绅的。
二十一条整合起来,严正公整,巨细无遗,桑知辛将其命名为《核税法》。
按他在朝中痛陈时所言,他翻阅了历年以来地方官吏勾结豪强作乱的案卷,发觉其中的核心便是税收。税收是地方豪绅一笔不菲的开支,他们与地方官吏的勾连,也是从税收的缴纳开始的,而他们挪用的粮食与银钱,通常也是从税收里克扣的。
所以,他这核税二十一法便是从税务入手,控制住地方官吏对税务的管理职权,使其无法从税收上牟利的同时,令豪绅无税法的空隙可用。
而与之相对的,则有庞大的体量需要撼动。
各处上报的耕田数量与田亩产量都需要重新核算,地方的税务与仓库,都要按着账册另外核查。
桑知辛言,此法若要施行,只怕要花费一至三年之久,但若落于实地,那么此后三五十年,都可高枕无忧。
据说朝堂上当即炸了锅。
朝臣们清算下来,能有几个干净的?桑知辛此举当真是狠极了,非但大义灭亲,还要将朝野上下的文武百官全都推上危墙,让他们跟着桑知辛一起倒霉!
当即,反对的奏折雪花似的送上了鸿佑帝的御案。
方临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一时都有些惊叹,这日在怀玉阁用饭时,还在跟赵璴感慨。
“那二十一条我也看了,桑大人此番当真是存了破釜沉舟的心思,要与满朝大半官员为敌。”方临渊道。“若这就是他的自救之法……桑大人还真是个够狠的人物。”
却见他对面的赵璴有些心不在焉。
“能以布衣之身爬上那样的位置,他定舍得开,也足够了解龙椅上的人。”过了一会儿,方临渊才听见赵璴说道。
方临渊闻言,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这么说,是因为他摸清了陛下想要清洗官吏,却又不好开口的心思,于是主动展示自己的用处,做陛下手中的刀刃?”他道。
赵璴却没声了。
有心事?
方临渊不由得转头看向赵璴。
却正好撞见赵璴从他脸上收回目光,安静地伸箸去夹菜。
只是他夹的那一筷子是他最不爱吃的羊肉,却见他夹走之后又放进口中,像是全然没在意吃的是什么一般。
肯定有心事。
方临渊多看了他两眼,直到赵璴注意到他的视线,抬起眼来。
“你今日遇到了什么事吗?”方临渊问道。“看你似乎有些累。”
只见赵璴微微一顿,继而看向他,道:“有吗?”
方临渊笃定地点了点头。
只见赵璴微一垂眼,停顿片刻后说道:“抱歉。”
方临渊连忙摆手,可两只手这会儿又拿着碗筷,一时间手忙脚乱的:“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闲话而已,你今天若是累了,就早些歇息,没什么的。”
却见赵璴微微一顿,继而看向他,说道:“我无事。”
方临渊正要说什么,却见赵璴已经站起了身来,一手拢起了宽阔柔软的衣袖,露出一截白出莹光的皓腕,另一只手跨到了桌那边去,夹起了一筷柔软的鱼腹。
“这是外头的人特送来的松江鲥鱼,说是肉质极细嫩,比京中的河鱼好些。”
说着,只见赵璴偏过身来,将那筷鱼腹放进了他碗里。
方临渊正被那筷鱼吸引着视线,却在这时,几缕幽香盈盈的发丝恰在此时垂落,落在了他的耳际。
……赵璴!
他将鱼肉夹来,恰好倾身,垂于肩头的长发便散在了他身上。
分明……只几缕落下的发,却偏冰冰凉凉的,又很香,像是将人缠裹住了的蛛丝一般。
方临渊又不会动了,眼见着鱼肉落进自己碗中,赵璴的声音又恰于此时在耳边响起。
“你尝尝。”
那是什么声音?是鲛人勾魂索命的低吟。
方临渊这些日真是靠近不了赵璴一点,此时通身僵得厉害,余光却恰见旁侧的赵璴微微偏头,问道:“怎么,是蒸鱼不合胃口?”
方临渊像是被提线的人偶似的,连忙拿起筷子,有些忙乱地将那块鱼放进了口中。
“嗯,好吃。”他胡乱地点了两下头,想让赵璴快些坐回去。
却见赵璴偏头看见他的反应之后,又道:“还可以吗?那我再给你夹两块……”
方临渊像是被鬼追了似的。
“不必!”他只觉自己头顶都在冒烟,连忙出言打断了赵璴。
似乎为了证明自己真不用似的,他站起身来,下意识地做了个极不合餐桌仪礼的举动。
他竟倾身而去,一把端起了那盘鱼,放在了自己面前。
瓷器与桌面相碰,发出细碎的一声响。而方临渊被这道响动惊醒,猛地发觉自己在做什么。
他……
怎么这样丢人!失了魂似的!
他别无他法,只得佯装不在意,将鱼放在面前,便坐下身去,埋头猛吃起来。
却未见旁侧一直默默看着他的赵璴,目光是有些偏移的,并没有在看他的脸。
他的目光落在方临渊的耳根上。
又是绯红一片。
一次能是偶然,但总不能第二次还是。
这于赵璴来说是陌生的。
它与他熟悉的厌憎、谋划与贪念不同,它炽热,却又纯净,像是天马行空的话本子里所描绘的词一般,诸如“情窦”、诸如“悸动”。
当真如此吗?在他与方临渊之间。
这种认知,让赵璴握着牙箸的手都收紧了。
他是披着画皮的妖鬼,和任何美好的词汇都不沾边。若是当真让他窥见这样美妙的一隅,他定会毫不犹豫地扑上去,抢夺、霸占、据为己有。
但是不行。
他怕一切只是他的癔症,他欲念侵邪之后生出的妄想。
他不能吓到方临渊。
所以,他只能强忍着,硬收着锋锐的利爪和叫嚣的獠牙,将自己凶悍的魂魄囚禁在眼下这副昳丽的躯壳中,学着那些女妖,去试探、去诱惑。
这令他仍潜在黑暗里,但又与他以往每一次黑暗中的潜行不同。
这回,他步步为营地,是要去碰天上的太阳。
赵璴的心脏又忍不住酥麻地战栗起来。
——
那日在大朝会上,对于桑知辛奏呈的核税二十一法,鸿佑帝不置可否,以至于两天下来,弹劾桑知辛的奏折不知凡几,其中更有言辞激烈、出口痛骂者,说桑知辛妖言媚上,就是为了遮掩自己的丑恶行径。
鸿佑帝一直没有回应。
直到两日之后,又在御书房外长跪许久的桑知辛,终于得到了单独面圣的机会。
那天,据说陛下只问了桑知辛三个问题。
三问之后,不知桑知辛说了什么,冷置他多日的陛下竟龙颜大悦,非但恢复了桑知辛中书侍郎的官职,还将核税法收在了御案之上,说要拿去由六部商议核准细节。
这在朝野上下,简直是平地一声惊雷。
陛下问了什么,桑知辛又是怎么答的?所有人都想知道他是如何化朽为神的,又打算如何处置他们这些昔日的同僚与旧敌。
朝中两派官员乱成了一团。
而方临渊得到这个消息,亦是震惊至极。
不过,他没像那些官吏一般急迫乱撞,毕竟再如何核查税务与财收,他都坦坦荡荡并不怕查。
唯一担忧的,就是赵璴。
他这日离了衙门,便径直去了怀玉阁。此时时辰尚早,怀玉阁还没布晚膳,窗外夕阳灼灼,赵璴恰坐在窗边,手中是拿着几封信。
“桑知辛的消息,你也听说了吗?”方临渊问道。“陛下怎会轻易放过他?”
便见赵璴没有出声,只是将那封信放在了他手里。
方临渊低头看去,便见那封信上赫然是今日在宫中时,鸿佑帝与桑知辛的对话。
方临渊诧异地看向赵璴。
便见赵璴平静地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看信。
方临渊垂下眼去。
信件上说,鸿佑帝见桑知辛后,桑知辛跪地行礼,鸿佑帝却未叫他起身,只是问道:“爱卿进献核税法,可有想过这些时日被审查下狱的多为你的门生亲故?”
便见桑知辛叩头道:“微臣不求陛下恕罪,但这本就是微臣的第一罪过。”
鸿佑帝没有说话,桑知辛则是继续说道。
“微臣识人不清,任用不忠不孝之徒,是微臣心瞎眼盲,以一己之错祸害了陛下的江山。而他们就任之后,微臣非但未行约束,反在有所觉察时只以为是无伤大局的小错,又担心越矩管束会有逾越之嫌,故而听之任之,酿成大错。”
看到这儿,方临渊都不由得要为他叫好了。
他说自己一时放任才造成如今的局面,鸿佑帝对他又岂非是一时纵容?倒是好一招推己及人。
“但若说结党,微臣绝无此心。只是朝堂之上多以同乡同年引为党徒,微臣即便无心参与,多年来也难免受同僚提拔点播,从中亦有获益,因此仍不敢奢求陛下原谅。”
信上说,当时的鸿佑帝无甚表情,只片刻后问他:“既是昔日同乡旧友,你竟如此狠心,连他们的性命都不要了?”
“我等的性命,皆是陛下的,是朝廷的。”桑知辛这样答道。“臣已错至如今,不可再错,进献核税之法,也不过只是想弥补一二。陛下若能采用,即便取了微臣性命,微臣仍别无二言。至于旁人,律法在上,青天朗朗,自也要如微臣一般,为自己的罪责承担后果。”
说到这里时,鸿佑帝的神色已然缓和了。
“你如此说,便是知罪了?”这是鸿佑帝问他最后一个问题。
信上说,当时的桑知辛,涕泗横流,泣不成声。
“微臣自幼不得温饱,侥幸长成,若无陛下,怎会有此后步步登天,侍奉殿前的机会?微臣今日的全部,包括性命,全是陛下赐予的,办砸了陛下的差事,微臣恨不得以死谢罪,以偿陛下的大恩!”他说。
“但是微臣一死容易,决不能留下一摊乱局给陛下。于是微臣负罪含恨,即便与朝野上下、与四境官僚为敌,也要替陛下扫清污秽!到了那时,微臣背负骂名而死又有何惜?只要不负陛下大恩,便是千刀万剐,微臣也在所不辞!”
看到这儿,方临渊背后的冷汗都出了一身。
对症下药、巧言令色,又情深义重,这能在御前长盛不衰的人,当真是有过人千百倍的手段的。
他读完了信,看向赵璴的神色有些怔然。
“他……”方临渊一时说不出话来。
说句大逆不道的话,若他是陛下,有臣子在他面前这样声泪俱下地陈词,他也是会动摇的。
隔着一张信纸,他都对那人生出了忌惮。
他语塞,却见赵璴只微微摇了摇头,说道:“秋后草虫而已,多跳两下,反倒合了我的心意。”
方临渊不明白赵璴为什么这样说。
却在这时,一阵寒风恰好吹来。窗子没有关严,那风径直吹开了窗,猛地撩起了赵璴垂落的发丝。
也将身上披着的外袍吹落到肩侧。
方临渊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赵璴穿得太单薄了。许是屋里没人伺候,他衣袍穿得随意,此时一阵风过,竟露出了他一段白而细腻、骨骼匀停的肩头。
方临渊脑中又是一阵滚烫。
这姿容分明染上了两分勾栏劲儿,衣衫不整,发丝逶迤,可这模样却偏生是在个男人身上。
男人……
赵璴还记不记得他是个男人啊!
热气都快蒸到方临渊脸上去了。他飞快地指了指自己的肩头,对赵璴示意道:“外头风大,你穿厚些,当心着凉。”
赵璴却似乎没听懂他的话,只是起身去关窗。
“房中还好。”他说。“府上地龙烧得早,还有些热。”
谁让你关窗户了,让你穿衣服啊!
方临渊身体里的热劲儿来回乱窜,一会朝上一会朝下的,厉害得很,让他不由得心惊,对自己和赵璴都产生了畏惧。
他只得咬牙,直起身来,越过榻上的小桌,便要亲自去给赵璴将衣服拉起来。
可他神识有些纷乱,便使得动作也略莽撞些。
他伸出手去,一把提住了赵璴滑落的衣襟。
也同时地,温热的指腹,猛地划过赵璴肩上的皮肤。
作者有话说:
方临渊:离我远点,我报警了!!!
赵璴:(无辜眨眼)勾引自己夫君还犯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