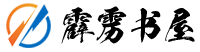王公公的手艺便是放在宫里也是一绝。
方临渊一口气点了好几个菜, 没一会儿,便有侍女一道一道地端了上来。
蟹粉浓香醇厚,配上清爽的豆腐恰是一道相得益彰的好羹。桃酥饼是拿掺了桃花蜜的油煎出来的, 油香中满是花蜜的清甜。小厨房里的羊肉更是新鲜的山羊羔肉, 不必太多配料, 只需拿火一催,其中的肉香便全激发了出来。
最后, 两碗汤分别放在了方临渊和赵璴面前。
“这是王公公特做的银杞茉莉汤,里头还特加了川穹和白芍。王公公说,殿下与侯爷劳碌了一日, 这汤最是安神解乏, 还可明目。”
听见侍女这样说, 方临渊不由得问道:“殿下今日在忙什么?”
赵璴淡淡抬眼看向那侍女。
可那侍女是侯府里的, 不大看得懂赵璴的眼色,这会儿方临渊跟她说话,她一双眼也没往别处去看。
“啊, 是庄子上送来的秋收账册。”那侍女笑道。“岁朝姐姐说,今年各地收成都好,账册也就繁杂些, 便尤其令殿下辛苦了。”
方临渊不由得转头看向赵璴。
便见赵璴神色平静,只淡淡看了那侍女一眼道:“好了, 不必多嘴,下去吧。”
那侍女笑着朝他二人行了礼, 飞快地退了出去。
“账目很复杂吗?”方临渊不由得看向赵璴。“要是麻烦的话, 交给岁朝就好了, 她从前年年都替母亲处理这些。”
便见赵璴摇了摇头, 说道:“闲着也是无事, 当打发时间。”
方临渊不由得佩服他。
朝堂上如今都要闹翻了,赵璴却仍是这般岁月静好的模样,当真是大将风姿,让人佩服极了。
不过,说到账册,方临渊又想起了另一桩事。
“说起来,今年佃户们的地租,原本就是你垫付的。”他说。“我之前看账,四万两白银呢。这回对完账册之后,你就划到你的账上去吧。”
正喝汤的赵璴抬眼看向他:“这是做什么?”
方临渊一脸理所应当:“还你的银子呀。”
赵璴拿着汤匙的手微微一顿,便听方临渊笑道:“我也不是跟你见外,但是这么大的侯府,还是公私分明些,总不能老让你吃亏的。”
“不算吃亏。”只听赵璴说道。“垫进去的银子,本也就是你打马球赚来的。”
打马球?
方临渊一顿,便想起赵璴所说的正是清明那日,他与王昶比试那回,赵璴押注重金那件事。
这不是混淆了嘛!若无赵璴的本金,这些银子会从哪里来?
方临渊张了张口,正要说什么,却听赵璴淡淡笑了一声。
“不必分这么清楚。”他说。“反正现在公账私账都归我管,全是我的,何必倒来倒去呢。”
方临渊一愣,才意识到赵璴跟他开了个轻快的玩笑。
他与赵璴目光相触,忍不住笑出声来。
“好啊,原是将主意打在我整个侯府上了?”他说着,伸手夹起桌上的羊肉,笑道。
“那也行,既不分你我,日后王公公便是我的人,我请他做什么菜他就得做什么菜。”
便听赵璴也笑起来:“悉听尊便。”
一时间,柔软的气氛在席间荡了开来。方临渊浑然未觉,只低头吃着羊肉,再抬头时,一碗蟹粉豆腐已经放在了他手边。
暖融融的灯火下,他与赵璴相对而坐。窗外夜色静谧,他笑着,赵璴眉眼上也在笑着。
竟真如长流的细水,轻飘飘地流淌而过,直朝着看不见尽头的远方而去一般。
——
窦怀仁度过了一个无眠之夜。
他去卫戍司耍了一通威风,只当是在给赵璴示威。
毕竟他可是在帮着赵璴做谋权篡位的事,他们两个就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
更何况他才是一家之主,是顶天立地、可以坐皇位、可以传血脉的男人,赵璴做什么都得靠着他,怎么能不好好地供养他?
他那是外室吗?那可是专门替赵璴养的、替他篡权夺位的!
窦怀仁心下不服,便打定了主意,既赵璴不能让自己过得舒服,便也要赵璴尝尝家宅不宁的利害。
却不料,回到府中,他迎接的竟是和嘉公主的怒火。
赵璴告了密。
赵璴将他打算带着外室南下的事情,告诉了和嘉公主。
“窦怀仁,倒真是我轻看了你。”和嘉公主怒道。“原你不是没本事,而是所有的本事,全都用在对付本宫身上了!”
“谁对付你了?不是你说我窝囊,嫌我仕途不顺吗!如今陛下遴选官员南下,多好的机会,我难道不全是为了你公主殿下的颜面吗!”
窦怀仁梗着脖子与她争执。
但和嘉公主却从不是与他讲道理的人。
话音未落,一个耳光已然落在了窦怀仁的脸上。
“你拿我当傻子骗,是吗!”她嗓音尖锐,提起裙摆扑了上来。
这天,直到半夜,窦怀仁才捂着脖颈上抓出的血口子,灰溜溜地钻进了书房。
……赵璴,原是赵璴!
两人争执之间,窦怀仁才在和嘉公主的骂声中知道了真相。
原是赵璴知道他去卫戍司后,便派了人来找和嘉公主。她身边的那个松烟,死人脸似的老嬷嬷,板着脸请和嘉公主规劝他。
说朝中之事不是五公主一个女流之辈能够左右的,之前那对母子本就是窦怀仁假借名目放进她私宅里。此后看在先皇后的面子上,五公主才稍作收留,眼下断无法帮窦怀仁与那女人私奔。
好……她倒是把他的老底全都揭给了他夫人!
窦怀仁回到书房中时已经气疯了。他忌惮和嘉公主的高贵身份不敢与她争执,可赵璴又算什么?要说把柄,难道他手里没有吗!
窦怀仁发疯似的翻起了书房里的暗格。
他这里,可有的是赵璴谋逆犯上的证据!只要拿出来,赵璴还敢这样不把他放在眼里吗……
信件翻出来,窦怀仁哆嗦着拆开。
这封不行,上头既没有重要信息,也没有赵璴的笔迹;这封也不行,信不是赵璴写的,上头非但没有赵璴的名字,还有他想要自己的孩子登基为帝的狂悖之言……
一封封信翻过去,窦怀仁的后背上渐渐泛起了冷汗。
几十封信件……赵璴在这里头,像是隐身了一般。
没有落款,字迹不明,没有任何与赵璴有关的线索,一封一封,全是他窦怀仁在谋逆……
赵璴……这个贱人!
她早就做好准备了!许多信都是东厂送来的,阅后即焚是东厂的规矩,他不敢跟那群活阎王讲道理。至于其它的……什么信烧了,什么信没烧,他竟全然没在意过。
可是他送给赵璴的信,数都数不过来……
天色微明之际,窦怀仁靠着宽大的水曲柳书桌,颓然地滑坐在地。
这贱人早就筹算好了,难怪他一点都不怕他,随便就将他的事情揭露出去……
可是她忘了!她一个女流之辈,离开了他这位舅舅,还能做什么!
他只管等着!
除非赵璴不想要她的大业,不然,他的儿子总有一日能登上皇位。不管是谁,就算是和嘉那个泼妇生的,也是他儿子。
片刻之后,窦怀仁笑了起来,神色几近癫狂。
赵璴这贱人,只管等着吧。
老天把她生成个女人,就是要她永远都要被他压住一头。
——
与陛下的千秋宴不同,迎接外使的礼节虽说繁杂,但仪仗所需完成的也不过是骑马列队、整装开路而已。
几日的操练,方临渊带着十六卫的兵马们将迎接来使的队列、礼制、路线以及行进的流程全部操练过之后,又演习过两回,基本能全做到万无一失了。
那日卫尉寺少卿与他说的话,他半句都没透露给他们。因此这帮小子至今仍将这差事当做天大的恩赐,操练时也恨不得拼尽十二分的功夫。
有时糊涂些也是好事。
数日之后,眼看着波斯国与缅甸国的使臣便要进京了。
这日操练过后,正是黄昏时分。兵马司送来了迎接来使那日所用的马匹。
都是高大健壮的大宛驹,毛色是清一色的雪白,上百匹白得发光的高头大马送进卫戍司时,引来了周遭不少百姓的围观。
“当真是好马啊!”李承安这样见惯了好东西的公子哥都忍不住感叹,围着分派给他的那匹白马转了好几圈,伸手去摸骏马的鬃毛。
“这是朝廷特养来用作仪仗的马匹,自是不同。”方临渊在旁侧说道。
“那咱们之前演练时都没骑过,过两日外使进京的时候,会不会出岔子啊。”旁边有人问道。
“这些马匹本就是自幼遴选出的,秉性稳定,善于服从,况且在兵马司中也日日操练,就算是你出岔子,它们都不会的。”方临渊瞥了那人一眼,笑着说道。
卫戍司的兵士们不由得纷纷发出叹息。
“我爹前两日还特送了我一匹好马呢,看来他送的马是派不上用场了。”李承安在旁边笑嘻嘻地说道。“不然转送给您吧,将军?那白马漂亮极了,您正好拿去送给夫人。”
送马?赵璴似乎不喜欢马。
但说起送夫人,方临渊微微一顿,想起了赵璴这些日在家中管账的辛苦。
“你自己留着吧。”方临渊道。
那边,几个卫兵还在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
“波斯国他们年年都要进贡异兽,听说今年陛下整寿,进贡得尤其之多,咱们能不能降得住啊?”
“谁让你降异兽了?人家都在大笼子里关着呢。”
“嘿,那我还真想看看,究竟是什么模样。”
“你没看过?我可是年年都看,当真是世所罕见的奇景……”
周遭众人说着话,方临渊却走上前,拉过李承安道。
“倒是有另外一件事,你过来,我要问问你。”
——
两日之后的一大早,方临渊便领着十六卫戍司的人马候在了南城门前。
高大的白马列阵而立,马上的卫兵身被金甲。金甲之上红缨飘荡,卫兵手中立着高高飘扬的幡旗,远远看去一片漫卷天地的金红,像是射落人间的朝霞一般。
礼乐司的人马分列两侧,手中抱着的乐器不胜枚举,在日头下闪烁着熠熠的华光。
而安平侯府内,则是一片安宁的静谧。
今日外使进京,许多条街道都戒了严,无论官民都是不许踏足的。
因此府中的下人们今日大多也没有出门。
赵璴窗外,绢素领着一众下人在院里清扫昨日落的积雪。赵璴静坐在窗下,正静静地对着棋谱研究一盘死局。
棋局正是焦灼。白子势如破竹,黑子溃不成军。只是尚未到全然分晓的时刻,垂垂挣扎之际,许也有生机暗藏。
赵璴单手捏着黑子,已然垂眸沉吟了许久了。
就在这时,吴兴海急匆匆地从外头进来。
“殿下。”他迎到赵璴面前,将手中的一封信件放在了赵璴手边。
“什么事。”赵璴微微拧了拧眉,看他一眼,将黑子放入棋盘之中。
“安平侯遣人送来的,说是急信,半个时辰之后,与您有要事相商。”吴兴海说道。
赵璴放了一半的棋子锵然落进了棋局之中。
一盘复杂的棋当即被震乱了。赵璴却不顾这些,一手飞快地拿起那封信件,已然从坐榻上站起了身来。
“可有说是什么事?”他一边拆信,一边飞快地吩咐道。“去备我出行的衣服……”
信件展开,却见里头只短短一句话,是方临渊的字迹。
“车驾已备,不必更衣。”
——
今日外使入京,方临渊在外带队,按说该是没时间与他见面的。
若要此时相见,便是急事。但看方临渊信中的语气,却不像急事。
赵璴停在原处,眼见着吴兴海已转身去取他的衣服了,便先行出声制止了他:“等等。”
吴兴海回头,便见赵璴单手握着那封信,神色莫名地看了片刻,继而说道:“无事,你不必管了。”
吴兴海不解,却仍是躬身行礼道:“是,殿下。”
他正要退下,却在即将退到门前时,又被赵璴叫住了。
“还是先派人去探听一番。”只听赵璴说道。“窦怀仁、太常寺还有卫尉寺上下,全部与今日外使入京有关的,去查他们可有异动。”
吴兴海躬身行礼之际,不由得多看了赵璴两眼。
只见五殿下目光已然平静下来,似乎信中不是要事。可他偏又要派人,上上下下地全要查上一遍……
吴兴海微微一顿,继而在心中不甘而认命地叹了一声。
这样谨小慎微,殿下若不为了他自己,还能是为谁呢。
——
赵璴换上了一身出行的百褶遍地金罗裙。如今的天气已是日甚一日地寒冷,他外头穿了一件软红的织锦袄子,又添了一件兔毛披风。
以女子的身份出行向来麻烦一些,即便不特作装扮,他赶到府门前时也是一刻钟之后了。
马车果然停在那儿,赵璴微微偏头看了一眼,便见车夫正一边行礼,一边躬身朝着他笑。
马车一路穿过静谧的街道,熟稔地绕过每一条禁行的道路,拐了几个弯后,停在一条人来人往的后巷里。
赵璴打起车帘,已然有侍女将下马的足凳摆在车前了。
赵璴目光微扫,便见周遭往来的皆是身着锦衣、非富即贵之人。他面前已有满脸堆笑的掌柜领着一众小厮上前跪拜迎接,他抬头看去,只见面前是一座三层高的雕楼,走的是偏门,因此看不见这座楼的牌匾。
他没有出声,只抬手让面前众人平身。
那掌柜当即起身,躬身笑着一路将他迎到了三楼。
“今日得蒙公主殿下驾临,真是我泰丰楼三生之幸呐!”那掌柜一边将他朝三楼的尽头带,一边笑着说道。
泰丰楼?
赵璴的确没来过,只听闻此为京中最贵的酒楼之一,又颇受官家纨绔公子的偏爱,因此声名赫赫。
他没言语,旁侧的绢素已然替他问道:“掌柜怎么知道公主殿下会来?”
那掌柜一边笑着,推开了三楼尽头两扇宽大的雕花门,一边说道:“安平侯爷对殿下上心呐,昨日特花了重金,托了好几位公子才替殿下您定下了这里!咱们泰丰楼,那可是今日遍京城最好看的去处了!”
雕花木门被推了开来。
微微凛冽的寒风忽地迎面吹来,而周遭众人眼中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三面临窗的顶楼厢阁,宽敞而华美,柔软的帘幔被敞开的窗子灌进的风吹拂起来。
正中的圆桌上,珍馐满桌,却只一副碗碟,虽未摆放美酒,却隐约能闻见母树滇红的香气。
而他们正对的床前,赫然是一座宽敞的露台,透过那儿,正能看见一路通往皇城的长街。
“异兽过长街!那可是每年万寿节上京城最好看的奇景!侯爷听说咱们这儿是观赏异兽的妙绝之地,专程为殿下定下了这里!”那掌柜说着,忽地惊喜道。
“殿下您瞧!时辰正好,使臣的队伍过来了!”
说着,他一路将赵璴请到了露台之上。
天际晨光明亮,长街两侧的门户与街巷口,挤满了前来观礼的百姓。
而长街的南端,雪白的骏马与金甲的士兵,已经平稳地举着飘扬的旗帜,缓缓朝着他们的方向走来。
伺候在旁的掌柜都不由得小声叹道:“今年的排场当真浩大!”
列队的兵马两侧,恢弘的礼乐声在长街上荡开。被仪仗簇拥其间的,除却那些奇装异服的南洋使臣之外,便是一座又一座、望不见尽头的巨大兽笼。
鬃毛烈烈,通体金黄的巨大狻猊,露在兽笼之外的巨大兽首威风凛凛,可见一双金黄的眼瞳与两对锐如利剑的獠牙。羽毛光亮、尾羽拖曳的白孔雀隐约泛着金光,像是山海传说中穿云带雨的巨大神鸟。
唯独传说中才有记载的仓光,皮肤厚重如同重甲,长吻之上竟有一只独角,与山海经所载一模一样。
还有长鼻巨耳的巨象,被牵过长街时,青砖地面都跟着微微地发出战栗。
恢弘,奇异,热闹而又繁华,像是照入人间的异界神景一般。
这儿果真是遍京城观礼的最佳所在,一年一度异兽过长街的奇景,唯独在此处观瞻最为震撼。
周遭众人的眼睛没有不发亮的。
他们小声讨论着,一会儿说这异兽模样威武,一会儿又指着说看那个美如神降。
独被簇拥其间的赵璴一言不发。
众人都在看异兽,谁也没注意到,只有他,一双眼明亮而专注,深邃如漫天星辰坠落,在这遍天下都罕见的奇景当中,唯独看向了一个方向。
那是白马上的金甲将军,率众策马行过长街,在经过泰丰楼时,飞快地朝着顶楼的方向眨了一下眼睛。
看异兽的众人自然谁也未曾注意,唯独赵璴看见了。
他知道,意气风发的小将军,是将这片奇景作为礼物,在送给他。
赵璴笼在袖中手微微地战栗,在谁都没看见的地方,仍攥着那封信。
他收到了。
非为什么奇景难得,而是漫天遍地,什么东西,比得上他一番炽热的心思呢。
作者有话说:
赵璴:呜呜呜,他也爱我,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