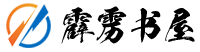他慢慢走上去,裴司琛让了让位置,于是楼道狭窄的窗口外,云间泄漏出来的一点余光又将人的眼睛照亮。
光影以一种荒诞陆离的方式在空中浓缩。
南嘉恩有些着急地在裤兜翻找着钥匙。他两手都拿着东西,以往很容易拿出来的钥匙今天却怎么也找不到,并且他右边还有一道不可忽视、炙热的视线,这加剧了他的心慌意乱。
钥匙被摸出来的一瞬突然掉落在地上。南嘉恩也被吓了一跳。
他弯下腰正想捡起来的时候,一双手先一步覆了上去。那人手背青筋明显,隐忍着所有的情绪,不动声色地替他捡了起来。
两人一同蹲下的时候头离得很近,这次就不再是报纸上看到的了,而是近在咫尺。额头、眉眼、鼻梁、嘴唇,都被细碎光影照顾到了。
裴司琛身上的味道又变了,很陌生,不再是熟悉的感觉,却还是很好闻。
“怎么这么不小心?”裴司琛很平静地打开了这道原本会破门而入的门。
人一下子从阔大的地方走到此处,会有一种突兀的拥挤感,逼促、低矮、乏味。
房间不算很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看不出有什么会离开的想法,大概是想要长久居住在此地,屋子各个角落被布置地很用心。
譬如阳台摆了一面的绿植,在五月中旬里,被照料得很好,花草迎着风和光在抬升。电视机还有专属的帘布,门背上还挂置着他的背包,厨房里的冰箱上贴着很多颜色各异的小玩意儿。
不再是昏暗笼罩,而是彩色、亮丽,似乎是住在这里很幸福、快乐。
房间的主人总是不长记性,就这么让人进来了,似乎觉得裴司琛不会做什么事情,只是进来看看。他随着裴司琛的目光也观察着房间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如惊弓之鸟般等待裴司琛的审视。
裴司琛伸出右手抚了抚桌上的一对杯子,那还是南嘉恩在超市打折买到的,他微微抬眸问:“恩恩,你很喜欢这里?”
南嘉恩还站在门边,两手拿着东西。听到这里,他终于有了点勇气看向裴司琛的眼睛。
“因为很喜欢这里,所以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是不是这样?”裴司琛慢慢走向他。
他抚上南嘉恩的腰线,目光专注认真。
衣角被慢慢抬了上去,这具贫瘠的身体正在发出细细的颤抖,裴司琛想起来,就跟胆小的家猫一样,很害怕的时候也不会出声,紧闭着嘴,窝在一角一动不动。
“恩恩,你是不是以为我不会难过,你走得那么爽快,完全不给我缓冲的机会……”
“如果我没有办法找到你呢,那是不是就再也看不到你了。但目前看来,你过得很幸福。”
幸福二字落声很重。
身下人似乎是心虚,对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反抗,最多只是紧紧抓住他的手腕,然后又被立马压了回去。
“对…对不起,我不应该…”南嘉恩慌忙地说着抱歉,到底是他先离开,认为是自己不对。
但是裴司琛摸着他的下唇,纠正说:“不对,你不需要抱歉。你又没做错什么,最多是让我不太好找。先前是我做的不对……”
裴司琛俯在他耳边,声音压得很低。
“我就不应该放任你离开,之前对你太温和了…应该把你的手和脚锁在一起,最好是眼睛、耳朵都蒙上,让你看不到这里所有的一切。”
南嘉恩身上的衣服用料不是很好,触摸上去都是粗糙的质地,这个天气他只穿着一件白T恤和黑色牛仔裤,上衣如今已经被拉到了脖子上,裤子还半掉不掉地挂在膝盖上,最后又堆积在脚腕上。
他身上的味道一如既往地很好闻,有驱蚊的花露水的味道,还有他的沐浴露清香。
裴司琛细细地闻着,从脖子闻到了衣服里。
随着裴司琛冰冷的手触到了他的裤子里,南嘉恩手上的东西终于掉落在地上。
香瓜还是完好,但是蛋糕裂开了,奶油和芝士倒成一团,样子很不好看,弄得塑料盒到处都是,变成这样都没有食欲了。
裴司琛的手指转了转,于是南嘉恩很容易地就被带着起起伏伏。
台风天过后的艳阳里,这所屋子还算是阴凉,他贴近了质问:“南嘉恩,你怎么那么快?”
这话让南嘉恩直接抬不起头,他很受不了地塌下腰,祈求着:“你不要……”
他冷白的后颈被人紧紧抓着,距离更近之后,便直视着裴司琛的眼睛,再是他幽青的瞳孔,发出冷光来。
南嘉恩突然回想起台风那一晚无光的黑夜。
“不要什么,你下面/容纳得很好。”说是如此,裴司琛还专门带着南嘉恩的手拉了下去,也想让他感受一下自己的水。
“不要做,求你了…..”南嘉恩快要发不出声音来了,裴司琛的眼神狠戾又深沉,看着很恐怖,他眼角终于溢出委屈又羞耻的泪水,红了眼眶。
重力失衡,他突然被人抱了起来。
裴司琛让他把所有的重量都附在自己身上,猝不及防地,南嘉恩眼睛迅速睁得大大的,迫不得已抱着他的头。
“应该是我来求你。”裴司琛再一次纠正他的错误,“南嘉恩,我求你不要离开我,求你乖乖呆在我身边。”明明应该是祈求的语气,裴司琛说出口后,却变成一种意味深长的警告语气。
他感受着裴司琛的动作,这样的姿势对于南嘉恩来说就像是在受刑,他艰难地用手抓着裴司琛的背,又因为重力,手只能够着他的肩膀。
“疼….轻…轻一点,太深了。”南嘉恩眯着眼睛看了一眼下面,又惊恐地收回了视线,他感觉是要被劈/成两半,徒然地想减少一些疼感,用手捂着肚子。
外面的阳光大好,裴司琛还是背着光,有一些光线直直地照耀在南嘉恩脸上,他时而觉得热,又觉得冷,置身于火热之中,却又立马跌进幽蓝的冰水里,他没有办法,试图想要阻止裴司琛更深一步。
“放我下来……”
南嘉恩眼泪越来越多,明明上一会儿觉得今天实在是美好的天气,下一刻却变成如今的不堪的样子。
裴司琛抱着他,一步一步地在这个房间行走,自作主张地带着南嘉恩熟悉各个角落。
南嘉恩已然意识模糊,每逢感觉要往下坠落的时候,又被人抱着腰往上抬,他实在是不能继续了,手指甲掐进了裴司琛的手臂里,断断续续地说告诉他,说自己肚子不舒服。
裴司琛让他的脸刚好正对着阳台,此时已经是日落黄昏,远眺而去,掠过树林,昏黄的天和灰色的海滩连成一条不透明的横线,几缕海上白烟被余晖衬得苍凉。
他吻了吻南嘉恩的发顶,“你看,外面的天气多好。”
南嘉恩离开后,有一段时间裴司琛开始看电视频道、或者是听车里面的天气预报。特别恶劣的天气会被提前播报出来,这些城市的名字裴司琛都会注意。听上一遍后,他又做别的事情了。
就这样习惯性每天从头到尾听上一遍。
他希望南嘉恩走后,不要去做什么危险的事情,比如坐很高的摩天轮、没有防备心地去夜店、接触到比他心思多几倍的人……或者是去一个天气不太好的城市,诸如此类,裴司琛认为,如果南嘉恩好好告诉他的话,他会陪着他一起离开。
但是一切都晚了。
裴司琛再次过上了这种焦虑不安的生活,只是相比年轻时焦虑钱和徐妍的身体不一样,遇到南嘉恩可能会碰上的事情,都会多想到许多危险的层次,到处都找不到人后,时间线会不断拉长,他常在早上四点就醒来了,这种焦急又难捱的心情南嘉恩怎么会懂。
在C城还未出发,天气预报就说Z城有台风天。那时裴司琛表情就不算太好。
但是他完完全全掩盖了自己颓然、烦躁、忧虑的一面,那些情绪又变成了畸形的情感——暴戾、愤然、偏执,还有找到南嘉恩那一刻的豁然。
听到南嘉恩发出微弱的哭音,奇怪的是裴司琛感到很舒心、安然。
为南嘉恩漂泊无定的糟糕心情在这一刻平和起来。
他勾着唇角告诉南嘉恩:“恩恩,已经快要六月了,该回去过夏天了。”
似乎只是认同南嘉恩赶来这个靠海的小地方只是暂时来过一个美好的春天。
海边的云,到了天黑的时候还有几抹颜色各异的余光。风很温凉。
陈景良带着医生往上走。
他在跟着裴司琛手下工作之前,就已经跟过裴明成,再是集团创始人之一裴长升。
陈景良被丢进裴家的那一刻,就知道和做狗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他十七岁就跟着裴长升做事,但是做得事情大多是不干净,让裴长升干净的西装沾染不到恶臭的血便是他的职责。
那个时候裴氏集团还没有因为时政变成如今被整改的模样。因为心思缜密聪慧,陈景良被裴长升认为是一只有脑子的好狗。而在一次交手中,裴长升直接将他拉过来挡刀,陈景良垂死而生后,就再次认清一个事实——狗的命十分低贱。
演好一只狗比安心做狗更难,因为狗的忠诚是演不出来的,那只能以一种伪善的假面匍匐在主人的跟前。
陈景良其实和裴司琛接触不多,在这一年他才开始在裴司琛手下工作。
常人或许以为裴司琛只是想来集团分一杯好羹,夺取利益,但实则不然,裴司琛对集团的一切都不感兴趣,没有像他伯父裴松的野心勃勃。
裴松是一个狠毒狡猾的人,以陈景良的评价,这人最喜欢倚老卖老,一个让人以为马上会躺进棺材板但总死不掉的臭骨头。他胆子大,即使愚蠢但是敢拼敢冲在前头,跟随他的人还不少。
裴司琛便是一个很难外露私人情绪的存在,虽然知道很多,但是从来不做多余的事情。
他唯一一次失态,陈景良记得是一次刚走出昌耀大楼。那时楼下有一个些许驼背的男人,背着挎包,戴着黑框眼镜。裴司琛从车上就看到了,没过几秒就开门走过去了,他拉住那人的手臂,几乎是一秒之后,又说着抱歉放下。
不是他。
裴司琛背对着他,肩膀很奇怪地动了动,在那儿站了一小会儿,又很平静地走了回来。
陈景良知道他在找人,而且不太好找,南嘉恩的背景他也不敢翻太深,整个国家那么大,大大小小的城市如此之多,找人简直是大海捞针。
陈景良认为很多人是不存在爱情的。爱情具有欺骗性,在人感到轻快舒爽的时候给人错觉,其实单纯沉溺于随意变幻的性,但误以为这就是人世的爱情。但也有接触一些不需要爱情这种感性情感的人。
在此之前他以为裴司琛不会为这种事情冒险。
他不理解。况且陈景良认为没有野心的裴司琛在集团是坐不长久的,那么多暗流涌动,陈景良不认为他会遭受得住。
直到在股东大会过后,裴松没有得到原属于自己的位置大变脸色,他问裴司琛是不是在找人。
裴松善解人意地告诉他:“我很会找东西的,要不要我来帮你找?”
“但是要是被我先找到了,你该怎么办啊好侄子?”
裴司琛隐藏着的事情被人知晓后,在一段时间就变了样子。
陈景良觉得很熟悉,后来发觉,裴司琛有了裴长升的样子,狠绝、薄凉无情,他开始大改,安排了一个专门的小组查清集团内部的账目,连续几日弄得集团上下人心惶惶,很可观的,裴松的手下贪污得最多。
好巧不巧遇上政策变动,集团先一步进行了大清洗,好歹大厦没有哗然瓦解。但这只是打断了裴松的一小块脊骨,他依托积攒的人际关系继续苟延残喘、养精蓄锐。
飞机因为台风天不能起飞,裴司琛和他一同站在玻璃窗前看阴沉沉的天,这样浓黑的天也憋不出一滴雨水。
陈景良难得好奇,问道:“下一步要怎么做?”
此时集团还在内斗,裴氏外表光鲜亮丽,但是内里早已自上而下地烂透了,裴明成做不了什么大事,该保护他妻子儿子的时候不敢上前,到目前局势复杂,又带着人去了国外看病。
某种意义上,裴明成也是深爱徐妍,但是很虚势、荒芜便是了。
裴司琛便为了寻找到这样的人接下了一堆糟糕的烂摊子,还可能染得一身脏血。
良久以后,裴司琛才回答他说:“找到后就关起来。”
南嘉恩还是被找到了。
午后,陈景良坐在车内,刚好看到从斜坡处走上来了一个样貌和照片相似的人。
那人走路半低着头,好像不看前面的路也是可以走得很熟悉,马路鸣笛的时候,他终于抬起头来了,脸很小,比照片瘦削很多,便凸显出来人的眼睛很大,瞳孔颜色比常人深了许多,一种静默、纯色的感觉水清见底。
他们对上了一眼,南嘉恩还是看着前方,没有在意陈景良的注视,但也可能是不会觉得有人会这样观察他。
陈景良想,原来如此。好像裴司琛在意的人应该是这样,那种干净的样子就很适合当一只听话的宠物。
晚上十点,陈景良带着医生敲了敲门。
门倒是被提前打开了,裴司琛正站在桌前触碰杯壁的温度。陈景良将衣服和药品一同放在桌上。
南嘉恩发起高烧,医生进去看了看,看着满屋的凌乱,吸了一口气,然后熟练地拿出东西给他挂水。
送走医生后,陈景良告诉他,裴松负责的工厂今晚又进了几批货物,但是里面的东西暂且没有调查清楚。
裴司琛问他:“是从哪里运进来的。”
“南边。”
“有几天了?”裴司琛摸出烟但是没有抽。
“刚好一个周。”陈景良回答道。
“好,我知道了。”
“我们来这里的事情大概已经被他知道。”陈景良看了一眼卧室紧闭的门。
裴司琛点点头,但是没继续说什么。于是陈景良很专业地关上门离开了。
原本以为今晚就能带着人离开Z城,但是南嘉恩的发烧延迟了这一计划。
裴司琛拿出换洗的衣物去了浴室。浴室很小,他扫了一眼镜子柜,上面的洗漱用品包括牙刷都是一人使用,没有第二个人的东西。
洗完澡后,裴司琛刚走出来,便听到卧室传来很小的响声。
他推开门,南嘉恩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醒来了,此时坐起来,脸上一片病弱的红晕,眼睛也很虚虚地半睁开。
大概是烧晕头了,坐着没有怎么动。
裴司琛用手背摸着他的额头,感觉还是很烫,南嘉恩被他冰冷的手凉得往后退了一步,即使是生病,裴司琛也不能饶恕他在躲避,又将人拉了回来。
先是用酒精细细地给他擦拭脸庞、脖子…,再到手指,裴司琛擦得专注,低下头让南嘉恩靠在自己的怀里。
他问道:“还有哪里不舒服?”
南嘉恩意识终于回浅,但是头是剧烈的疼,全身上下都很不舒服,又是发烧又是被抱着他的人做到疲累,身体已然到达极限。
他声音很沙哑,第一句就问:“你怎么还在这里?”
裴司琛当即就停下来了,不再给他擦拭手指了。
然后怀里的人又低声说:“裴司琛,不要再做了。”
如今南嘉恩还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生怕自己就这样死在床/上了。裴司琛想,倒也没有什么值得怪罪的地方,况且南嘉恩这脆弱的身体再也经受不住折磨了。
于是裴司琛下巴靠在他的发间,轻嗅他虚弱的味道,安慰道:“不做了。”
听到这句回复,南嘉恩依旧是闭着眼睛,睫毛还是湿漉漉的,稍微有点安心地昏睡过去了,手指还微微勾着裴司琛的大拇指。
夜色下,人的脸被清幽的月色清洗。裴司琛看了他许久,也找了个姿势抱着他一起睡了。
第二天依旧是晴天,南嘉恩温度降下来了,只是还在沉睡。
裴司琛拿着水桶给他的花花草草浇了一点水,便去厨房看了一眼还在煮着的白粥。这里的厨具比不上别墅的高科技产品,但是裴司琛也曾生活在这种地方,半插着手,没有什么情绪地用勺子搅了搅粥。
门外传来急切的敲门声,而且那人敲门只够得着门一半的位置。
这便不是陈助理了。
裴司琛打开门,便看到一个只到他腰间的小男生,拿着个风筝拘谨地看向他。
张子扬本想来这里找南嘉恩一起去海滩放风筝的,无料看到了一个陌生的男人靠在门边。
他还没有看过这样的脸。应该是好看的。眼睛和常人不太一样,头发颜色也神奇,个子很高,感觉房间一下子变矮了。
“有什么事?”裴司琛面无表情地问道。
张子扬仰着脑袋,到底是年龄太小,怕的东西太多,比如被这人压迫性的眼睛盯得恐惧,他弱弱发声:“我来…来…来找嘉恩哥哥。”
“嘉恩哥哥?”裴司琛重复了他这句称呼。
“嗯,是嘉恩哥哥。”
“他不会陪你放风筝了。”
“为…为什么?”
“他身体不舒服,发烧了。”裴司琛简洁地概括。
“那我能看看他吗?”
“不行,他会传染给你的。”
“那好吧。”张子扬只好无奈说道,“那我改天来找他。”
裴司琛也很配合地说了句好。
于是门又被关上了。
张子扬捏着风筝,站在门口愣了有一会儿,半分钟后才慢慢拖着步子走回去。
到了下午点,南嘉恩还在沉睡。裴司琛站在床前看了看,最终做了决定将人抱了起来。
可能这里对于南嘉恩来说是避风港、安全屋,但是裴司琛不这样认为,南嘉恩应该呆着他身边,每天看着才会让人觉得舒心。
陈景良跟在他身后,眼睛瞄了一眼。
便看见一只青青紫紫的手臂,于是又淡定地收回了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