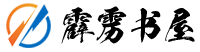惊雷四起,疾风骤雨倏地降临了淮北的土地,一时倾盆如注,风雨如晦。
已是黄昏,大雨泼在伞上,向周围滑下的雨水几乎成了道道雨幕,混着地上泥土,啪嗒响个不停。
“将军——”一个穿着蓑衣的将士从桐柏山上下来,来不及顾及脚下愈发厚重的泥块,朝白烬喊道:“堆积的山石已经清理开了,里面什么也没找到。”
林归才舒了口气,他正一手抱着白烬的剑,一边替他撑伞,在雨中站立多时,浸湿的鞋底仿佛是结了冰,他庆幸应如晦没给山石埋在下边。
白烬看着大雨面容凝重,他复杂的心里犹豫了会儿,道:“雨势太大,喊他们也都从山上下来,等雨停再做打算。”
“是——”那将士又踩着积泥往山上去了。
冬日的雨水寒冷砭骨,泥泞的山路崎岖难行,白烬实在不敢拿别人的性命开玩笑。
“小将军,下官来迟了。”雨声盖住了脚步声,周琮直接走到了白烬身后。
他身边有人给他打伞,便双手给白烬揖手行了个礼,周琮竟仿佛对一切都毫不知情似的,面色如常道:“还请将军莫要怪罪。”
白烬回想今日的事情,听到声音心底已然浮起了怒意,他转过身来,“周大人,你岂止是来迟了。”
天色渐晚,白烬的目光在昏暗的伞下看不太清,他的声音同往常一般清冷:“听闻周大人是从童慎那儿过来的,对衙门的事情,倒是毫不上心。”
寒风忽地就刮进了周琮的官袍里边,如同是根暗箭伤人猝不及防。
周琮像是冷得打了个颤,心底忽地浮起一种异样的悔意来,他今日恐怕是走错了哪步棋。
但周琮很快在寒风里定住了神,他在白烬面前依旧是那副诚惶诚恐的模样:“将军明察,今日下官集结了淮北的士绅在城西准备接待事宜,直到午后也没能等到将军的马车,是后来才听说了……童家的事情。”
“此事乃是下官被童当家的请到了家里,才知道了始末……”周琮叹了口气,“此事明明已经结案了,却出了如此大的纰漏,下官实在觉得无颜面见将军,以及……应大人,这才来迟了。”
“纰漏?”白烬的语气同大雨一般寒凉:“你的纰漏大抵是官商勾结露了陷,童子启假死脱罪不慎败露,你倒是有胆量,不等着我去抓你,倒是敢面色如常地走到我面前。”
“周琮,我不喜欢拐弯抹角。”白烬道:“你我立场大不一样,用不着花心思再来试探我,童子启知道的都已经说了,我现在并没有耐心和你虚与委蛇,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最好直接说与我听。”
周琮覆在一起的手猛然一顿,他从未在官场上遇到白烬这样的人,他几乎是毫无转圜地和他翻了脸,周琮缓缓将头抬了起来,那惶恐的表情从他脸上褪去,便是他万般筹谋的真面目。
周琮道:“小将军,凡事留些余地,总是对大家都好。”
周琮把伞从他身旁那人手里拿了过来,然后示意他先退出去,才又往白烬走近了一步,“将军来得不巧,这雨这么大,今日怕是上不得桐柏山,但结果我便先同将军明说,这山中什么都没有,来与不来结果都一样。”
“童子启自讨苦吃做了坏事,如今得了报应,落在你手里是他运气不好,但是白将军,若是只有一个童子启,你们此行怕是要失望。”周琮隔着两道雨幕看着白烬,“你入仕不到半年,朝中都说你是个追根究底的性子,但在这世间,毫不变通总是要吃亏的,你不妨再看看身边的人,再仔细想想可否还有两全的法子。”
一声惊雷“轰隆”在头顶炸开,林归撑伞的手一抖,那伞上的水混着雨往地里落,填出了个泥泞的水坑,天已经快黑了。
方寸的伞遮不住风雨,白烬的衣服已经湿了大半,他直着身子站在暗夜前,一步也没退。
“你以为你很了解我?”白烬也从雨后注视着周琮,他说话的语气似乎有些变了,像那寒冷的雨结成了冰,带着锋芒似的,“周琮,你看过多少朝中人,便要直言这世间如何,若不铺天盖地地淋上一场大雨,怎么能刨根究底地将真相抖落出来,山雨欲来风满楼,那第一场雨就会下在你的身上。”
“可笑。”周琮冷冷地笑了起来,“少年狂妄,我竟忘了你不过是个十七岁的小子,你那同乡的孟凛比你大上几岁,就不会说出这般的胡话了。”
“孟凛?”白烬似乎是迟疑了一瞬。
这丝迟疑被周琮捕捉到,“哦,忘了跟你说,今日童当家的也请了孟公子去他府上,雨夜凄凉,大概是想和他聊聊……”
周琮仰面道:“……何为失子之痛。”
一道雪亮的闪电划过森然的天空,把乌云都撕开了口子,雷鸣从中奔腾出来,大地倏然明亮了一刻。
周琮这时候才看清了白烬的脸。
足以撕破天际的寒光打在白烬的脸上,像是蓦地给他打上一层霜白,让那本就清冷的脸上结了冰,明暗里透出了拒人千里的冰冷,他眼里仿佛有一丝血色,冷漠里带了狠戾,竟是掩不住的沉沉杀意漫了出来。
白烬像是在咬着牙,他一字一句道:“周琮,方才的话,你给我再说一遍。”
“噼啪”一声惊雷乍起,仿佛在人耳边狰狞地怒吼一声,周琮身若雷击,他结实地打了个寒颤,接着便是寒意与突如其来的恐惧从心上蔓延到了四肢百骸。
他在那一刻仿佛是个杀神。
周琮不禁后退了一步,可暗夜里又闪出了一道冷光,刀剑出鞘的声音在大雨里不甚明显,却同那雷声一道在他耳边炸了开来。
白烬从林归怀里拔出了他的剑,手起剑落,那剑从周琮的头顶划出道弧线,正正砍上了周琮的纸伞,伞骨从空中折断,那竖起的伞偏头一倒,翻进了污浊的泥水之中。
倾盆大雨依旧哗哗地淋下,落在泥水里,敲在伞面上,也浇在了周琮的身上。
周琮在大雨中后仰着摔倒了,被泥水溅了一身,他仿佛落在水塘里,湿乎乎的衣袖浸满了刺骨的冷水。
“你……”周琮这回脸上的惶恐是真的,他仰头看着,“你大胆,我依旧是朝廷命官,我是淮北巡抚,你怎么敢动我……”
白烬提剑往他走近了一步,他不顾雨是否落在身上,他将那话又说了一遍:“你以为你很了解我?”
白烬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周琮,你觉得我循规蹈矩的不敢杀你,可我早已不是从前的白烬。”
“你敢拿孟凛来威胁我,但他从来不是我的软肋,他是一把连我都会刺的软剑。”
周琮仿佛坠进了冰窟,他腿软着瘫坐在地上,全身湿透了。
脚步声由远及近,山上的将士踩着泥坑,从桐柏山上撤了下来。
几十人穿着蓑衣,队伍齐整地到了白烬面前,白烬看着面前的人,又瞥了一眼周琮,冷冷地下了命令:“周大人神思不大清明,去扶他一把,让他淋雨醒醒脑子,诸位与我,去童家高楼避雨。”
“是——”
天地在风雨中怒鸣,骤雨全无停下的迹象。
***
夜幕将至,风雨交加。
暴雨来得突然,淮水码头上人流如梭,水位涨的过于迅猛,童家迅速派了人去码头,诸多货物浸不了水,正连夜挨个封箱抬走。
童家高楼之上,童慎备了饭菜,与孟凛和吴常相对坐着,没人动了筷子。
其实童慎并不耐烦听周琮的在这里招呼这两人,他盯着吴常看了会儿,语气不善:“孟凛,你身边就跟着这么个残废?”
孟凛眼眸半沉,看不出喜怒:“不彰人短,童当家可要嘴上积德。”
“积个屁的德,老子什么德行谁敢管我。但是你这个人……”童慎好像想到了什么,他眼睛半眯了下,“我瞧他有些眼熟,他叫什么名字?像是以前见过。”
童慎仿佛被些久远的记忆突袭了,他更仔细地想了想,却被门外一声大喊给打断。
“大当家的——”门从外面被拍开了,童慎的一个手下慌里慌张地跑了进来。
童慎立刻心头火起,“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码头上人手还不够吗?”
“不是,不是……”那人被童慎的戾气一扫,慌张得变了结巴:“是……是那个刚,刚来的将军,他……他带了人过来,像是来……来砸砸砸场子的。”
童慎瞟了孟凛一眼,冷哼一声:“他倒是来得快,不等我去找他。”
“那当家的,我们该……该怎么办?”
“当然是拦下来!”童慎一脸凶相,“让剩下的人都去,别让他们湿了老子的楼。”
他咬牙切齿一般:“敢抓我的儿子,等这里事完,老子就去好好招呼他!”
那手下应声出去,童慎回过头来,他看着一桌子没动的饭菜,不耐烦道:“孟凛,你是觉得我委屈了你,这菜这么不合胃口?”
孟凛半晌不出声,直到外边的脚步声全都远去,童慎的人都被派去拦白烬了,孟凛才缓缓摇了摇头,“菜是好菜,只是我这个人有些毛病,风雨凄凄,须得拿些凄楚不堪的往事下酒,人人讳莫如深的真相添菜,逼问出来的实话作饮……”
孟凛如往常一般温雅地笑着,“童慎,我怕你请不起这顿饭。”
孟凛嘴里的话与那幅笑脸着实不合,童慎仿佛没听懂:“你说什么?”
待童慎下一刻再将话过了脑子,他那多年行走刀尖的身体先是嗅到了丝危险,接着抬手便握住了手边的刀把。
大刀扬起的一刻吴常动的更快,他面前的菜盘里放着切肉的短刀,刀口锋利,吴常单手拿起便对童慎扑了过去。
童慎怒目圆睁,大喝了声:“孟凛!你什么意思!”
吴常眉目若磐石,他眼里只盯着童慎手里的刀,对面横刀砍来,他擦着刀刃偏身而过,稳着下盘避免与他缠斗。
孟凛正撤到窗边,抬手便将个杯子砸碎在了窗棂之上,陶瓷声碎,正与惊雷一道乍响,“轰隆”一声,窗户伴着风雨大开,顿时窜进个灰袍人,带着满身凛冽的寒气从窗户进来,风雨呼啸,几乎填满了整间屋子。
那灰袍人两手各拿了把刀,他对着吴常大喊一声:“常叔接刀——”
吴常后退一步,他手中的短刀犹如暗箭朝童慎飞去,随即稳稳地将那灰袍人抛去的长刀接在了手中。
长刀在手,吴常目光骤然一厉,犹如出鞘的利刃。
灰袍人抱拳对着孟凛单膝跪下了,他微微垂眸:“陈羽拜见公子。”
孟凛“嗯”了一声,他身后是狂风骤雨,一道闪电凛冽地劈开天际,他眼中森然,再不笑了,他的声音顺风而来:“把他抓住。”
陈羽应声而去,与吴常一左一右将童慎围住。
童慎啐了一口,“孟凛,老子看走了眼。”
他谨慎地退了两步,与两人成三角之势,童慎不敢妄动,沉目看着两边,他脑子里忽地一惊,对上吴常那猛然锋利的眼神,“你是……”
童慎终于想起了往事, “无常刀……你是宁府旧人——吴常。”
“武林里的宁家满门被灭,一个都没活着出来,无常刀销声匿迹二十多年,如今竟然是个断手的残废。”童慎低低地笑了起来:“无常刀没了右手,你又能奈我何!”
童慎面色狰狞地看向孟凛,“那孟凛,你又是何人!”
“孟凛……”童慎念了遍名字,忽地呼吸一滞,他眼中闪过诧异,仿佛是恍然大悟,“是……宁家的女儿嫁给了那个姓孟的,你如今的年纪……你是孟明枢的儿子!”
童慎咬牙切齿,面露杀意:“我童慎不做行善积德好事,但也不做通敌叛国这等不齿之事。”
“贼子!”
作话:
其实我还挺喜欢这一章的(挠头.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