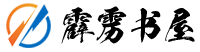灼热的阳光射进窗户,正午的热意将蝉鸣都堵得静谧下来,空气中仿佛安静了半晌。
“你说是齐恂。”白烬握着剑柄几近抬起,“你有什么证据?”
“年轻人。”塔尔跶一脚踢开了些地上的弯刀,“我为什么要来骗你,那年日头正午的时候得到你国太子的口信,我将家书放进盒子交给了前来的使者,呼云才回了奚族的宫殿,可她受了欺骗郁郁寡欢,死在一个阴天的正午,我再也不想正午听到噩耗,午休身边再也不想见人,不然你今天怎么会有机会见到我。”
塔尔跶抬着眼与白烬对视,一瞬寂静的空气里,白烬从他些微带着浑浊的眼里仿佛看到了历经风霜的苍茫过往。
塔尔呼云……五部奚的女子生得同中原的姑娘并不一样,白烬从记忆里找了许久,似乎是从母亲的闺中密友里找出一位生得如同劲风一般的姑娘,那位他记不得名字的姑姑曾念着他的名字,跟他说过几句听不懂的奚族语。
后来白家家破人亡,白烬从离别与苦难中与自己和解,又从仇恨中抽离怨言,带着决心走上一条注定不与旁人倾诉的小路,他从司马菽嘴中问出塔尔跶,又从塔尔跶嘴中问出了齐恂。
事情仿佛是连成一串,无人知晓背后到底会是什么走向,司马菽不过是个言官,而塔尔跶为了妹妹和族人,立场的不一分不出是非,那齐恂呢?齐恂又为了什么。
齐恂已经是一朝太子,以他的声望,只要将来稳步地等到当今传位,他有什么理由做这个恶人,有什么理由要牵连旁人的性命呢?
白烬实在想不出他白家哪一步拦了齐恂的路。
这家仇与冤屈已经让他背负了太久了,缓缓行进的路他走得荆棘丛生,他自己也不知道将来会去往何方,唯有沉住气才能长久地打算。
“好。”白烬后退了步,他把剑插回了鞘中,“我信你。”
“你……”塔尔跶似乎惊讶了一瞬,他又笑了,“你要是生在我奚族,也当是个好少年。”
少年……白烬没发表感想,他只又道:“我还有一事想问。”
塔尔有一瞬的犹豫,但他坐得身姿挺拔,如同磐石,“你想知道的我已经告诉你了,你还有什么想说?”
白烬站在几步之外,他带了种不卑不亢的姿态,“你奚族内乱,却还是塔尔将军前来出征,我想问的是……你是木昆氏的将军,出兵大宋,是谁的主意?”
塔尔跶怀疑地目光看去,“你到底是想要说什么?”
“多年前五部奚臣服大宋已经定下合约,尤其你木昆氏诚意明显,可毁约本就是不义,难道这次的举动,是你木昆氏主动为之吗?”隔着距离,白烬敛眉道:“我听闻……你是为了一族的性命出兵而战,可是你此次回去的前途性命,你族……”
草原上弱肉强食,塔尔跶打了败仗,如今掌权的辱玉氏本就容不下木昆氏一族,战败之后可能更要归咎罪过到他们身上,所以塔尔跶这次归去,多半是要凶多吉少。
白烬停顿给了塔尔跶反应的时间,“将军,我这里有一条明路,你可否要考虑一下。”
塔尔跶听明白了,他怀疑的目光又化开进沉思里,他许久才沉声问:“你有什么样的路?”
“我要你给我一封自愿臣服大宋的书信。”白烬往前走了两步,小将军仿佛带了种威压的气势,“信中写明当初开战并非你木昆氏的初衷,又自愿臣服大宋同意和谈条件,而且其中公正与否,还要听凭和谈使的要求。”
“和谈的条件?”塔尔跶眼里露了锋芒,“我五部奚岂不是任人宰割?”烟扇町
“不义之战。”白烬停在原地,“哪怕你不愿同意条件,和谈使一样在凉州向辱玉氏谈判。”
“靠上大宋。”白烬沉下了眼,他几乎面无表情,“今后才有一线生机。”
靠上大宋……一线生机……
塔尔跶风霜的脸上动了动,他的一双手多年勒马挽弓,年纪大了就有些形如枯木的征兆,他看了眼手心里的风霜痕迹,他自问英勇无畏,他为了一族而战驰骋草原,可他却是败了,但这一败涂地,就要如此将本族的性命置于险境吗?
塔尔跶沉思了许久,他把枯朽的手伸到面前,“好……我写……”
黑色的笔墨书写在牛皮纸上,信纸封进信封的那一刻白烬心里仿佛落了块石头,他却听塔尔跶对他道:“白,你叫白烬……”
塔尔跶抬起头颅,对着他清冷的眉目看了会儿,“你想留着我的命,是想有一天,为了白延章的事……”
白烬把信装进怀里,他却是没有回答,只一言不发地转头就走。
这空荡的大殿唯有日光洒进来添上明亮与阴影,白烬在塔尔跶的目光里一步步走向大门,仿佛是穿越了隔代的烟尘。
“白小将军。”陈玄在门口等到了白烬。
他看着白烬的脸色,又闭了嘴,陈玄在门外将能听的与不能听的听了个大概,让他几乎不知如何评判,这些事……自家公子都知道吗?
还有……公子交代他的事,怕是要就此推翻了。
“孟凛今日要你来的打算,我知道。”白烬看了陈玄一眼,“塔尔跶如今还要留着,兵行险招……我不牵连孟凛。”
陈玄一愣,他这是说的什么话?却一时不知从何反驳,“白小将军,公子也是一心为了你好,恕……”
陈玄干脆抱拳道:“恕我今日听到了不该听的,里头那个人要是不死,您要做的事情万一泄露出来……来日招惹的祸事怕要更多,就怕……”
陈玄不乐意说出不好的话来,只好作罢。
白烬深思了片刻,他问:“陈玄,司马菽,你认识吗?”
陈玄一时怔住,他抱拳的手都连带停止了下来,白烬在他的沉默里已经知晓了答案。
“罢了。”白烬将陈玄合在一起的手托了一下,他很认真地去看他的眼睛,“你同你家公子说,我不需要他为我做这些。”
白小将军说话不带过多情绪,却像是不动声色地直来直往,讲话一股脑说清楚了,其中的真意与虚情一览无遗。
陈玄低头受着这目光,心里仿佛忽地被什么撞了一下,原来这些白小将军都是知道的吗?那公子……
“……”陈玄还在思考时白烬已经往前走去了,陈玄作罢,只好赶紧跟了上去。
出古漠别院也很顺利,白烬同陈玄已经走到了街上。嬿陕廷
边境小镇人潮汹涌,来往的车辙声淹没进街上的喧闹中,平静得仿佛未临战火。
“陈玄,你先回去吧。”白烬忽地转过身来对陈玄道:“孟凛一个人在客栈,你也当去关照他的安危。”
陈玄觉得其中很有道理,便应声去了。
看陈玄离去的时候白烬站在原地,人潮如织从他身侧走过,他仿佛是立于汹涌江河中的石柱。
等到陈玄消失,白烬才绕路进了个偏僻的巷子,他撑住墙缓缓地呼出几口气来,胸口的位置竟是有些揪心的疼。
这熟悉的疼痛几乎将他的思绪拉到了前世,可能是他前世思虑太多,身体生了些毛病,大怒大悲之下,胸口似乎就堵了一口气一般隐隐发疼。
尤其今日说到白家的往事,又说到了齐恂,白家未洗的冤屈掀起了未能收复南朝的遗憾,朝他胸膛上狠狠倾轧过去,让他不得不记起事关齐恂的恩怨——
距离如今再过上好几个年头的前世,白烬南下出征,秋日的枫叶同战线连成一片,红得比鲜血还艳。
临到阵前,眼看着南朝的军队跨过了岭中,两军交战,唯有拼死一战方有生机,朝中却是私下派了人来传旨。
那朝里来的内宦挥着手里的拂尘,“白将军,朝廷的旨意,是退兵。”
白烬是征南军的主将,他尚且沉着气盯着那内宦,楼远却是先道:“将军,南楚兵马已经入驻岭中,若是过了天缺一线,便要直奔淮北,我军若此时退兵,岂不是……”
楼远言辞恳切,焦急地望着白烬,又瞥了一眼前来传旨的朝中太监,咬牙道:“岂不是要把我大宋疆土拱手于人?”
“楼少将军多虑。”那内宦眼高于顶地扫了他一眼,细着嗓子道:“朝中已定文官前来议和,此事就不劳诸位费心了。至于白将军……”
内宦谨慎地查看了下四周没有别人,这才朝座上的白烬敷衍地拱了拱手,“陛下薨逝的消息还未传开,几日后新皇登基,怕朝中生变,又无人堪当守卫皇城大任,所以白将军还是赶快领旨回京吧。”
“你们什么意思?!”楼远按地而起,气道:“白将军乃是陛下亲封的征南大将军,你们哪里是打的守卫皇城的主意,如今南朝虎视眈眈,你们居然想要撤军?这分明是……”
“楼远。”白烬眼皮跳了跳,拦住了楼远的出言不逊,他抬眸冷冷看向传旨的内宦,“陛下遗诏里,定的是哪位皇子?”
“这……”内宦犹豫道:“此乃密旨,白将军回朝自然得知。”
“密旨?”楼远心急口快,“朝中有那么一位党同伐异的太子殿下,难道他还能把位子让给齐越那个草包不成?”
“楼少将军慎言。”那内宦脸色泛黑,又把目光转向白烬,“白将军只管接旨,抗旨的下场,前朝那位秦裴大将军,还不够给您当做前车之鉴?”
白烬手间一紧,怒火攻心一时逼得他胸口微疼,这时楼远已经跳起身来,“你个阉人!秦老将军忠君报国,皆是朝中人有负于他,如今你们居然又来威胁白将军,当真是欺人太甚!况且白将军乃是……”
楼远意识到自己失言,当即闭了口,之后的话几乎是呼之欲出,白烬是秦裴的弟子,此等重蹈覆辙,简直是逼人太甚了。
白烬捏紧的手心却是缓缓松了,他抬眼看了那内宦,竟是连冷意也收起了,带着些无所谓的平淡:“朝廷的旨意不可违背。”
“将军!”楼远蹙着眉着急。
但白烬不紧不慢道:“可本将军并未收到旨意要回京。”
“你……”那内宦气急道:“你什么意思?军营里的人可都看见我进来,怎么能算没人传旨?”
白烬从那主位上缓缓站了起来,他当即走到了那白面太监身边,“喊你来此,是太子殿下的意思吗?”
那内宦吹胡瞪眼似的,“太子殿下的旨意难道算不得旨意吗?”闫单町
“并非如此。”白烬抬起一只手来,他冷静地凑到这内宦的耳边,“我只是可惜,南朝的人杀人无度,闯进我方将营,竟是……”
白烬的手握在了一旁的刀柄上,他眼中闪过一丝冷光,“当场杀了朝中贵客……”
那内宦只觉脖颈一凉,他不可置信地看着血从冰冷的刀尖上流下,耳边只听到一句:“你说这够不够理由找南朝开战?”
“你……”内宦捂着脖子,沉声地倒在了地上。
楼远眼里一亮,大仇得报似的拍了下桌子,“这不长眼的太监,早就该杀了。”
白烬将刀一把扔下,哐当地落在了那宦官的身侧,他冷漠地再瞥了一眼,“喊人过来收拾收拾,尸体和话都原封不动地送回朝中,给太子殿下……”
“齐恂。”
“齐恂……”从前事情的发展让人始料未及,齐恂作为一国太子,争权之际竟是做到了和谈这个地步,白烬如今站到他的对面,本是因为前世的结局,可如今,齐恂身上竟是还要牵扯到白家的家仇了。
白烬在原地缓了些,他挪步往街上走,想着从前胸口疼的时候是如何缓解的。
“掌柜,麻烦替我,斟一壶酒来。”
借酒浇愁……孟凛不得而知,从前白烬,竟是在往后的岁月里学会了喝酒。
作话:
旅游一时爽,赶榜火葬场……呜呜呜
酒都喝了,下一章试着写点那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