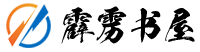孟凛被疼痛与席卷而来的记忆给包裹了——他骑着马在猎场飞奔,忽然就有一根长箭擦过焦灼的空气,“倏”地一声追着他的后背,沉沉地从后没入了他的胸膛。
孟凛疼得整个人都在颤抖,他感觉喉间的凉意愈发明显,沉重的四肢好像灌了铅,他整个人都伏在白烬的后背上,只用一只手死死地抓住了白烬的衣角。
但他听着白烬在前面对他无尽的呼喊声,孟凛没办法回应,他心中只缓缓升起了被命运轮回死命敲打的无力感,他忽然觉得绕了来回,他所做的一切都像是命运轮转、殊途同归,原来他依旧要经受这一箭,或者依旧要离白烬而去吗?晏衫挺
孟凛的眼皮渐渐沉了,他开始看不清白烬的后背,然后沉沉闭上了眼。
随后他觉得整个世界好像忽然被冰天雪地给覆盖了,他连呼吸到嘴里的都是冰碴的味道,压抑的味道刺激着孟凛的感官,孟凛好像在奄奄一息的时候睁了下眼。
这是……孟凛倒吸了一口凉气,眼前迷蒙的火把虚影与一个离去的后背在他眼前混成一团,胸口压抑的疼痛与铺天盖地的寒冷全然占据了他的思绪。
他是在做梦吗?他这是身处……刑部大牢?
周遭黯淡成亘古的黑暗,唯有耳畔接踵而至的风雪声提醒着他生命在一点点逝去,一点点将他沉没在无尽的黑暗里。
“我怎么会在刑部大牢?”孟凛自问,他又绝望地嘲讽了自己:“我为何会不在刑部大牢,一场大梦做得真假部分了。”
的确是真假不分了……
所有的重来与希望,此刻都在孟凛心里湮灭,仿佛这冬日纷扬的大雪,还能一道将他的心也给冻上。
孟凛不知道在黑暗与痛苦里忍受了多久,他分明记得自己经受过这样等待死亡的无力,可此刻竟依旧如此令人绝望。
好像时间够长,他感觉自己身体都虚浮起来,他随着长夜的风,缓缓地离开了刑部大牢。
孟凛好像混混沌沌,只跟着大牢外清晰可见的脚印,跟着那雪里的路一直往前走,可他竟然在那雪路的尽头,看见了白烬的身影。
白烬孤身一人跪在雪地里,纷扬的大雪往他的身上飘去,几乎在他肩头附上了一层冰霜。
孟凛好似忽然清醒了些许,他心里变得又焦又急,他想喊白烬起来,可他发觉自己依旧发不出什么声音,他连去触碰白烬也做不到,他只能眼睁睁看着白烬跪在雪地里,与他一道经受这漫天大雪的寒冷。
这时候……孟凛记起来了,白烬是才从刑部大牢里见过了自己,自己冷言冷语地告诉他,是他通敌叛国,做尽了伤天害理的蠢事,要他莫要再与自己扯上分毫的关系。
这话若是重来,孟凛是决计不会同白烬说的,可如今孟凛即便后悔莫及,也换不回一个曾经了。
京城里的寒风冷得冻人骨髓,风凌迟一般往白烬身上刮过,他的眼神仿佛是给冰雪冻住了,他冒着风雪缓缓开口:“不肖子孙,来京城数年,无所作为……”
孟凛的心里骤然一紧,随即他意识到白烬所跪的方向指向白家先祖,但白烬这些年来万事求得明理公正,他怎么会无所作为。
是……是自己当时所言北朝再无可救的话伤了他吗?
白烬嘴里的话并未停下,他一字一句地望着祠堂的方向:“未能遇奸小而处之,以振世道;未能匡扶社稷之危,救民于水火;未能……平南壤之战乱,以全国土。”
“未能承先贤之遗志,全……白家之名声。”
白烬咬着牙,每个字好像都在戳着自己的脊梁骨,世人都难以承认自己力不能及,难以认清自己荒唐一生、毫无用处,可白烬句句所言,皆在自省里藏着后悔与怨恨,仿佛不愿放过自己似的言明出来。
一个个字同样敲打在孟凛的心口上,白烬一人多年踽踽独行,其实走得举步维艰,没人知道他求什么,却依旧要一声不响地往前,片刻都不能停下。
可孟凛明明知道他求什么,却是一意孤行,朝着与白烬背离的方向越行越远。
孟凛不停地摇着头,他在白烬面前跪下,他想告诉他并非如此,可他只能看着自己的手像个虚影穿过白烬的身体,仿佛与他的距离,已经远至同一个世界之外。
“然……”面前的白烬忽地猛然低下头,他紧咬的牙关好似被什么锁住了,后话堵在嘴里,仿佛用尽了气力也难以言说,孟凛猜不出着难以启齿的后话是什么,才能让死生不惧的白小公子这般紧要牙关。
“然,心有私念,于世不容。”白烬终究是开口了。
孟凛伸出去想拥抱白烬的手猝然停在原地,他抬起的眼睛仿佛隔着时空与白烬对视,心有私念……白烬难以开口的,不过是心有私念,他跪在雪地里面朝先祖,想要求得原谅的,竟不过是动了从前不该有的念头。
因为自己吗?
孟凛不知道陪白烬跪了多久,白烬忽然地从雪地里拔出了他结了冰霜的剑,他怔怔地往门外走,却在外面遇上了过来的林归,林归望着白烬冷若冰霜的脸说:“刑部大牢您不用去了,孟公子他……”
“刑部那边说是畏罪自杀……”
紧接着白烬的长剑坠地,他狼狈地往后退,他竟然不可置信地说:“我不信……”
白烬就这么在孟凛的眼里,沉声倒在了地上。
呼啸的冷风从孟凛耳边刮过,好似将他这一刻又割得体无完肤,原来方才白烬难以启齿的私念是自己?他谨守礼义了这么些年,竟然要为了自己而违背他一直所信的忠孝仁义吗?
孟凛后悔了,倘若他那日没和白烬说些杀人诛心的话,没在迷蒙无知的时候将他深藏的真心漏出来,没有压抑了许久又情不自禁,没给白烬一点点不舍的端倪,此刻的白烬,是不是便不会如此……难舍难分?
一场大梦做得太真实了,他本可以……和白烬相互扶持,和他相知相伴地过完那一生。
所以……面前的才是结局吗?
孟凛心里灌了铅一样,本就被冰天雪地冻得止步不前,又被沉没得越来越深,没入了无边无际的严冬里。
这天地的雪又仿佛忽然停了下来,夜里的寒意刺骨,他好像还是跟在白烬身后,白烬披着夜色出城,他像个黑暗里的独行者。
孟凛自知只能做个旁观者,他贴在白烬的身侧,仿佛还想再多看看他的容颜,可白烬好似与上次相见憔悴了不是一点半点。
紧接着他才发现,白烬是去了乱葬岗,刑部大牢里每日都会死上一些囚犯,若是无人把尸体领走,就会把尸体丢在此处,孟凛是个叛国的罪人,他的尸体未被凌迟曝尸已是恩典,怎么会有人把他的尸身领走。
白烬竟然在这寒夜里,从那百具死尸中,找起了孟凛的身体。
好在这些日子冷得刺骨,就是尸体也不过被冻成了冰霜,白烬找到孟凛的时候他的尸身还未腐烂,但白烬默声地看着孟凛的脸,那早已并不十分清晰的面容,孟凛不知道他沉默垂下头的时候是否流下眼泪。
白烬再昂起头,他再有什么情绪也被他本就冷淡的面容遮盖住了,他背上了孟凛的尸体,一个人在寒夜中走了不知多少步,堪堪在天亮黎明的时候,到了另一片城外的山林。
白烬将孟凛的身体放在地上,他好像有些哽咽地说:“我为你寻了归处,旁人,旁人都不知道。”
孟凛颤抖着手要去触摸一下自己的面容,他忽然就涌出了眼泪来,他做了那么些荒唐的事情,白烬竟然还愿意为他寻一处归处。
白烬在一个人挖着地上的泥土,用的正是那把孟凛给他送过的长剑,孟凛心如刀绞地跪在他的旁边,他用手一道在地上挖着,即便他根本就碰不到泥,他还是与白烬一道做着那个动作。
他在陪自己心爱的人,为自己挖掘一道坟墓。
白烬默然地将孟凛安葬,孟凛在旁边张了张嘴,他发现自己还是无法言说,只好在心里默声地说了谢谢,这地方依山傍水,的确是白烬替他寻的好归处。
忽然间又是天地变色,夜里静得深沉,月色如水。
一个剑影快得如同虚影,一人执剑向孟凛的方向刺了过去,剑势如虹,直接没入他的身体穿过,那执剑人眼露杀意,越过了他刺向白烬。
孟凛心中惊慌地响过一声“白烬小心!”但他忽然看清了那执剑人的身形,他不由得心中一凛,这是……江桓?
白烬已然是换了装束,他手里的剑与江桓相撞碰出一丝星火,两个人擦着身子交错而过,又端着剑相对而视,细微的风从他们二人的剑尖略过,平添了几分剑拔弩张的杀气。
孟凛这一世再见到他们相遇,以为不过是江桓爱使些性子与白烬不合,但就是白烬也未曾跟他提起,他与江桓从前还有过过节,江桓眼里的杀意实在太过浓厚,孟凛不由地会猜测,他莫非是来替自己寻仇的?
白烬长剑侧身而立,一剑接上来未试出来着深浅,只问道:“你是何人。”
江桓只冷冷地扬起剑继续刺了出去,一边道:“孟凛……是你抓的?”
“孟凛”二字停顿了片刻,白烬的心弦仿佛在那一刻被拨动断开,他手里的剑不觉收了半分力道,后话再入耳时已经敛了三分锋芒,长剑一偏,竟与江桓的剑斜穿过去,白烬身形一闪,衣袖被江桓割破了个口子。
江桓抬眼冷笑:“你也不过如此。”
白烬半点也没看伤口,只冷眼抬眸,又字字明晰地重复道:“你是何人?”
江桓直言不讳,他昂了昂头,“江天一色,江桓。”嬿杉亭
莫名的关系好像让白烬有一刻愕然,好似就是从这一刻起他心里又生起了别的猜测,江家家主的江桓,竟会为了孟凛而大动干戈的孤身寻仇?
两个人缠斗的身影在孟凛面前来回而过,孟凛一遍又一遍地穿到两人中间,一遍又一遍地发觉自己无能为力,他看着自己两个至亲的人互为仇敌,仿佛要争斗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不断变换的场景之下,孟凛早已没了力气去拦,江桓几乎锲而不舍缠上了白烬,那几十次的刺杀连孟凛都数不过来,他几乎每次都会言明一些孟凛的身份,孟凛的名字又以不同的方式跟随在白烬身后。
世事如流水,孟凛好像跟着白烬历经了沧海桑田,从前孟凛害怕触及白烬不愿提及的过往,未曾问过他从前都经历了什么,白烬也是将他死后的一切轻轻揭过,可如今孟凛竟然亲眼见着白烬往后岁月,是如何过完他这一生。
刀光剑影渐渐远去,有一日江桓终于不来了,可是孟凛见着白烬,接过了南下平叛的圣旨。
白烬孤身一人走在偌大的皇宫,这个泥淖一般的深潭里处处都是虎视眈眈,白烬平静地接过旨意,他也平静地带着大军出发了。
可是世事难料,南朝的大军竟然直接越过了岭中,早一步向北朝开战,孟凛本还在疑惑为何如此之快,他竟然在南朝的大军之中,见到了江桓。
因为孟凛死在了北朝,江桓刺杀了数次未果,他竟然带着岭中投靠了南朝。
原来不过因为孟凛做了不一样的抉择,往后的结果会如此大相径庭,孟凛知道自己如今什么也改变不了,他只跟在白烬的身边,木然地看一个结果。
最后的大战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一刀刀划在白烬的身上,亦如同在孟凛心里添上一道道伤疤,白烬不顾朝中旨意继续南下,他没像他的师父一样被罢免官职愤然离场,而是拼了他最后一口气与南朝殊死一战。
可腹背受敌的大军没有活路,齐恂与南朝朱启明勾结,二人图谋两朝皇位达成协议,只要除去眼中钉,两朝的合议就还如从前一样生效,他们共分天下的坐上各自的皇位。
而沙场上的将士抛头颅洒热血,不过是做了无谓的棋子。
四处的火光灼灼地烫着人的感官,白烬杵着剑半跪在其中,他呕出了一大口鲜血。
孟凛无措地想堵上白烬的伤口,他想在白烬生死之际再护他分毫,可他只能眼睁睁地看人割破了白烬的喉颈。
白烬会同千百具尸体一道葬在天地之间。
孟凛已经泣不成声,他不知道白烬是死于战场,他不知道白烬死前经历了怎样的背刺,白烬从未跟他说过,他死于不公正的世道与毫无道理的背叛,可他竟然能在重来一世时不改心中赤诚,他还能一步步走得小心谨慎,甚至不忘了将他拉上一把。
孟凛捧不住白烬的头,接不住他的血,他只能虚虚地做出一个抱住他的动作,他想带白烬离开,也想替他寻一个归处,可孟凛不过是个早该归去的人,他没法带白烬离开这个地狱。
周遭的焰火已经要缓缓燃过来了,即便孟凛并无直觉,他亦觉得那火焰在烫着他每一寸的皮肤,但他不愿离开白烬的身侧,他在一片烈火里,片刻也不想和白烬分离。
仿佛如此他就可以和他一道同归天地。
……盐删庭
孟凛已经分不清什么才是梦了,他只在虚浮的天地间,一遍又一遍,无声地喊着白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