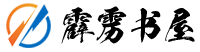“阿凛,阿凛。”银铃般的笑声在孟凛脑海里盘旋,他竟然听到了母亲的声音。
五六岁的孟凛个头不大,却从先生那里学来了端方的仪态,他从高椅上跳下来,给背后笑盈盈的母亲行了个礼,“母亲。”
那时的宁素素除了挽起的发髻与得体的衣物,活得还有些像个宅门关不住的少女,她拉过孟凛拱起的双手,把他的手翻了过来,然后神秘地把个什么东西到孟凛的手上,“这是你常叔送你的。”
钝感的触觉落在孟凛手上,他微微皱了皱眉,可在宁素素翻开手的时候,孟凛忽然眼睛一亮,“是木雕!”
宁素素笑着眨了眨眼,“你家常叔说你每日读书辛苦,给你做了小玩意来玩。”
那木雕刻的似乎是个小动物,趴在孟凛小小的手上,显得可爱极了,孟凛那个父亲连见上一面都难,平日没有人给他东西玩,孟凛的眼睛盯着那个木雕,“这是只小狗吗?”
“这是……”宁素素脸上笑意一凝,“这明明是只马。”
但宁素素又清了清嗓子,“你家常叔是想你如同野马奔腾,不受这世俗的约束,万顷原野长空,没有地方是你不能去的。”
孟凛心里觉得冒昧,却又一时被这世俗之外的话给惊住,他小心地把那小木马揣进袖口,“是我妄言,我去,我去亲自拜谢常叔。”
“唉——”宁素素伸手拦了下孟凛,却又觉得不当拦他,只好尴尬地笑了笑,“你去吧。”
孟凛不懂母亲这反应,只哼哧地四处跑去找着常叔,最后才在后院一堆木头渣子里找到了还在刻着木雕的吴常。
吴常见到孟凛过来还慌张了下,他生硬地把手背过去,“小公子……”
孟凛跑过去拉了拉吴常的衣袖,“常叔辛苦,我去给您倒杯茶水。”
然后吴常就看见孟凛转身去倒水了,他却在原地愣了半天,生生等到孟凛倒水回来。
孟凛把水端到吴常面前,“常叔请用。”
吴常呆愣地在身上擦了擦手,然后把背后的手露了出来,他不小心就给孟凛全看清楚了,孟凛竟然五六岁的时候就有了小心思,他故作惊讶道:“常叔方才是在刻木雕?”
吴常再缩回去也是无用,他摸了摸头,“是,想给小公子做点小玩意儿。”
吴常手里的木马已经刻了大概了,比方才宁素素给他的要像马多了,简直可以称得上活灵活现,孟凛忽然明白了方才宁素素拦他的深意——原是宁素素藏不住秘密,拿了个没刻好的就来给了孟凛。
孟凛把衣袖里的小马儿捂严实了,对吴常一脸惊喜道:“常叔好生厉害,这马刻得可算是活灵活现。”
吴常笑得有些傻气,“公子喜欢就好。”
“喜欢。”孟凛接过吴常喝完的水杯,“自然是喜欢的。”
吴常笑了笑,继续低头去刻着木马,吴常耍刀的手十分灵活,但刻起木雕可算是个门外汉,从旁边的木头渣子,也能看出他已经刻了好些遍了。
有些话孟凛不便说出口,可他知道吴常刀功非凡,理应是威风凛凛的,却愿意给他一个小孩子生疏地做着木雕。
连他的亲生父亲也做不到这个地步。
孟凛心里感动极了,他想:我以后一定要对常叔好。
对常叔好……
孟凛忽然觉得胸口一阵钝痛,整个人都是天旋地转的感觉,他深深地呼了口气,突然醒了过来。
他做梦了——他梦到了吴常,那时的吴常还双手俱全,给他做小马儿来玩。
可现在……孟凛猛然睁开了眼。
他喃喃地喊:“常叔……”
“第二十八声了。”江桓在孟凛的床边耷拉着眉眼,叹着气道:“他都喊了二十八声常叔了。”
王禁之从孟凛胸口处拔下一根银针,才深深地呼了口气,“人应该是醒了。”
江桓立即就凑了过去,喊了一句:“孟凛。”
孟凛脑子里全是乱的,他觉得身体哪一处都疼,左肩右手好似断过,胸口更像是压了块巨石,呼吸起来都觉得有钝刀子朝他的五脏六腑来回割过,喉间干涩得快要冒火,疼痛从他喉间传来,连张嘴都变得有些困难。
可孟凛醒来第一句话依然是:“常叔呢?”
江桓伸过来的手立刻停在原地,他难以启齿地动了动嘴,不禁闭上了眼。
孟凛眼前的血色一时又涌了起来,他脑海里来回闪过吴常被万箭穿心的场景,他哑着声音问:“常叔是不是……没了?”
孟凛这样子有些骇人,王禁之觉得没眼看,顾自走开去写药方了。
围在床边的还有陈玄,他“扑通”一声就朝地上跪了下去,低着头艰难道:“属下去迟了。”
这场景下没人说话,应如晦只好沉声道:“孟公子节哀。”
孟凛的心沉到了底,他的手在床上攥紧了,眼睛却直视着头顶上的床檐,一动不动地盯着那白色的床幔,眼里依旧带了血色。
许久孟凛闭上眼,一行清泪从两旁滑下,他松开手,也睁开了眼,“让我去见见他。”
孟凛昏迷了两天两夜,江家的灵堂早已经搭起来了。
吴常身上的刀箭是江桓亲手一把把一根根拔下来的,江桓自诩铁骨铮铮,他竟头一回在这血肉之躯面前也有所动容,鲜血染红了他的手,他替吴常闭上了双眼,带着他和昏迷的孟凛回了江天一色。
孟凛在灵堂外就跪下了,扶着他的陈玄也一道跪了下去,从门外到屋里的距离,孟凛一步步跪过去的。
吴常死了。
孟凛并非是个自欺欺人的人,那跪过去的一步一步里,他早已接受了这生离死别的事实,他见过许多次杀人的场景,他甚至在杀人满门后看着血色和火光全身而退,可他已经许多年没有见过,他的亲近之人死在他面前了。
上一次至亲死在他面前,还是……还是他相依为命的母亲。
那一次孟凛被吴常带着离开南朝,他在无数极端的情绪里对着一堵白墙痴坐了三日,不吃不喝,他几乎没了生的希望,本就虚弱的少年差点在无尽的黑暗里追上母亲的步子。
只是那时他还不能追随母亲而去,他要留着一口气将母亲的大仇报了,才有颜面去见她。
孟凛的那口气支撑着他杀人放火,燎了赵家满门的性命。
而那往后……往后他又遇着个人,这才贪图起活着的滋味来。
可如今,吴常死了。
他与吴常,并无血缘亲疏可言,可在他发了疯寻不到母亲时,在他蒙了心要与虎谋皮时,甚至在他要重新做一回人的时候,吴常都寸步不离地跟着他。
比起那对他利用算计的亲爹,吴常才更像他的爹。
这个爹像块怎么也挪不走的大石,为他无言地遮挡了大风大雨,却从来不与他吐露半分自己的情绪。
孟凛跪在吴常的灵堂前,满堂高挂的白绫像是给人胸口上束缚起一圈一圈的绳索,勒得他有些喘不过气来。
孟凛朝吴常的灵位磕了一个头。
他闭上眼就能再想到那日吴常被穿心的场景,吴常死前还死死盯着他的眉眼,他眉目里锁了几十年的愁绪却好像一朝烟消云散,平白多出几分释然似的。
这份释然更是戳得孟凛无处躲藏地后悔起来。
“那日我不该骑马出去……”孟凛不住地想:“我也不该,不该让常叔去问马车……”
“不对。”孟凛更多地往后想起,“是我不该抓了石七,不该折磨他在他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哪怕是杀了他我也不该放他回南朝……”
“我不该去试探孟明枢……”
孟明枢……
孟凛心里真的好恨。
“王爷的意思,不计得失,要让四公子亲眼看着,吴常死在你面前”——孟明枢这是在警告他,是在惩罚他,是在高傲地提起剑来,正大光明地戳在他的心口。
孟凛不过是不想回南朝,孟明枢就要如此告诉他,我等着你来取我性命。
疯子,孟明枢他就是个疯子。
从前因为母亲的遗愿不让他回南朝,因此就算孟明枢逼他离开朝廷,孟凛也没有再报复过他,可如今孟明枢步步紧逼,已经到了他退无可退的地步了。
后退只能任人欺凌,这一次,孟凛绝对不会再退让了……
岭中的天变得极快,昨日的艳阳今日竟乌云漫天,应景地下了一场雷鸣暴雨,张牙舞爪的闪电带着惊雷,仿佛要吓走不愿离去的冤魂,而骤雨冲洗着难以洗掉的血色与污秽。
孟凛羸弱之身,在灵堂里跪了三日。
江桓过去点香的时候查看了下孟凛的情况,他一言不发地摇了摇头。
这个虚弱的病秧子,在灵前再没流过一滴眼泪,他那模样,让江桓想起了十年前刚从南朝离开的孟凛。
那日黄昏,雨已经停了,树枝上低落着豆大的雨滴,西边却罕见地烧出一大片火烧云来,红得像是浸了血。
陈玄几经考虑,他走进灵堂跪在孟凛身后,“公子,南朝那边……又来人了。”
孟凛的脸被灵堂的火晃得有些阴森,他颈上伤口未愈,说话低沉:“他们怎么说?”
“还是……还是说接公子回南朝。”但陈玄立马就抓住手边的刀,恨道:“属下去杀了他们。”
“慢着。”孟凛略微偏了头,拿余光冷冷地扫了陈玄一眼,他嘴里停顿了片刻,“你去跟他们说,把石七活着交给我……”
孟凛阴郁地抬起了眼,“我就跟他们回去。”
作话:
岭中篇接近尾声,阿凛就要去南朝搞事业了
关于常叔看着孟凛的眼睛,其实是因为孟凛和他母亲的眼睛很像,但是这会幻视哈利波特和斯内普,怕被说融梗就没有写到正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