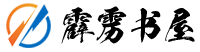爬山的事情被迫中止,苦了白烬带着一老一弱,下了山去。
见了江天一色的令牌,那壮汉不敢失约,雇了马车在山下等着,又将人送回了江府。马车穿过街道,隐蔽地走了后门进去。
孟凛拦下了王禁之掀帘子的动作,“此路走了后门,师父不必担心。”
见到这许久没见的半个徒弟,王禁之心里总有些不好的预感,从前在他身上砸了许多草药进去还没收回本来,现在还不知道冤家路窄会赔上什么。
王禁之摸了下胡子,他身子前倾,试探问:“孟凛,你是……知道些什么?”
孟凛却是笑笑,“我与师父许久不曾叙旧,师父怎么这般想我,等回了江府,还想请师父替我看看脉象。”
这倒霉孩子就知道贫嘴……王禁之收回了视线,听着车辙声继续在马车里晃悠。
回了江府,孟凛差人给王禁之换了身衣服来,他那爬山采药穿的衣物沾了泥,污得像身乞丐装,王禁之来的事孟凛嘱咐了不让人说出去,将他请进了自己居的院子。
又让人奉了茶进来,孟凛与白烬相对而坐,请王禁之坐在了正中的位置,然后紧闭上了房门。
孟凛见王禁之端起茶杯,浅浅地抿了一口,随即客套道:“岭中山野产的茶,不比皇城奉的贡茶,还请师父将就。”
“咳咳咳……”王禁之一口茶差点呛到,他顺了口气把杯子放下,眉目一横:“孟凛,你有话直说,不必在这里找我的晦气。”
白烬尚且不明状况,微微蹙眉看了孟凛一眼。
孟凛接过去眼神,立马给王禁之赔罪了:“师父得罪,跟你说实话,我当初去淮北祁阳,就是冲着您御医的身份去的,本来想托江叔叔找您行个方便,可您不愿居在岭中,怕您不乐意,才特意搬去了祁阳,还没有说穿身份,师父……您别介意。”
白烬不解问:“御医?”
王禁之沉下眉目重重呼了口气,捏着手里的茶杯没有说话。
孟凛看向白烬低着声音道:“禁之二字取由林示,太医院的前任院判正是林太医,你我相识的那位林净山林太医,我还能叫得上一句师兄。”
说起林净山,王禁之眉间才化开了些,“山儿如今,如今可还好?”
“林太医医术高明,又得陛下倚重。”孟凛忆起京城,会心地浅笑了下,“当初在京城时还多亏了师兄照顾,我的病他也替我瞧过了。”
王禁之掀起眼帘,“他怎么说?”
“……”孟凛沉默了半晌。
“也罢,我自己来看。”王禁之抬起手伸了过去,“你这是沉疴痼疾,我与你说的静心安养你可曾遵照?”
孟凛被白烬剜了一眼,只好苦笑:“师父的话我怎么敢不遵从。”
王禁之摇了摇头,他的手搭上了孟凛的手腕,号起脉来王禁之就成了严谨认真的一代名医,孟凛也就不敢再说话,静静等着他诊脉。
王禁之诊了半天,本就有些沟壑的眉头皱成了山丘,他摸了把胡子,先是白了孟凛一眼,“你……身子不好还纵欲……”
随即叹了口气,“今后还是要节制一些。”
“……”孟凛与白烬脸色“唰”地一下变得有些不好,孟凛喉间动了动,他赔笑道:“师父,师父说的是……”
王禁之“嗯”了一声,又疑惑地抬起眼来:“怎么?你如今婚配了?把姑娘带给我来瞧瞧。”
可他见了孟凛那有些难看的脸色,不禁猜测:“莫非你是出去……”
“咳咳咳……”这番轮到孟凛来咳了个不停,“师父,您怎么这么想我……”
白烬在旁挪动杯子发出了点动静,他恢复神色,解围似的道:“王大夫说的是,明日就嘱咐厨房替他好生调理。”
王禁之一脸“还是白烬懂事”的表情继续把起了脉来。
把脉良久,王禁之有些口干舌燥,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然后才满是忧愁道:“我不是告诉过你,凡事心宽,哀怨郁积于胸则气滞,气血不通,你又一直虚亏不满,最忌伤神动气,平日添衣适食,不可再生他病,只能温养,急躁不来,我并非逼问于你,但你自己想想,你都遵照了几条?”
伤神动气哀怨受伤,孟凛生生违了好几条,他没脸回答,只好低了头去不再说话。
王禁之把手收回去,“从前的方子暂且先不用了,我替你开个新方。”
他往桌上看了眼,白烬立即就起身去寻纸笔了,王禁之无语地说了孟凛一嘴:“凡事都让白烬替你做了,从前祁阳你就亏欠他良多,你怎么也不知道心虚。”
“我知道的。”孟凛抬头狡辩了句,他悻悻地把手撑在桌上,“只要他想要,我什么都赔给他。”
“……”王禁之尝茶尝出了味儿,又喝了一口,“我记得你们不是去京城了吗?白烬,白烬他……他师……他不是做了将军?我听说你考了状元,怎么如今都在岭中?”延删艇
白烬正拿了纸笔过来,“烦请大夫开药。”眼陕庭
王禁之话问一半,没等到孟凛作答,却接了纸笔,也就写起了药方。
老御医开起药来行云流水,行行药材写了满满一页,他还没抬眼,“依旧是一日早晚二服,莫要间断。”
王禁之写完了方子,拿起纸页掸了掸,他本欲将药方递出去,却手间一顿,又把方子收了回来。
“给你治了这么多年病,没治好你是我医术不端,身为医者我心里有愧,听你叫我一句师父,我也该说几句良言,但是孟凛……”王禁之支起头,“我听不得你跟我打马虎眼。”
王禁之把那药方折叠起来,收进了自己怀里,他神色严肃,“我没你师兄好说话,你今日请我过来,不单单是为了这一张药方,除了我从前御医的身份,你肯定还知道些什么,不然也不会带我走后门进来。”
王禁之当初在朝廷里呆了这么些年,他不是傻子,凡事看得出端倪。
孟凛盯着王禁之的动作看了会儿,露了个和缓的笑意,“师父刻意躲着朝廷,徒儿不是瞎子,如今岭中来了巡抚,自然不当暴露师父的所在。”
王禁之攥紧了手放下,他沉声道:“你怎么看出来的?”
孟凛面色从容,“师父当初离开朝廷,隐姓埋名,连林师兄也不知您的所在,本来厌倦朝廷辞官故里当是平常,徒儿不明其中因果,不应该妄加揣测,却是在白烬入朝之后,又见师父不见了踪迹,其躲避之意,当算明显了。”
“孟凛。”王禁之沉思了片刻,眼神带了点阴郁,“你不怕我不把药单给你?”
孟凛起身去给王禁之杯里添了点茶,他答非所问道:“师父可曾听过……白延章这个人。”
王禁之连带着白烬都有些手间一颤,一直不说话的白烬缓缓推了杯子,仿佛示意孟凛给他也倒上一杯。
滚滚沸水在杯中倾倒,孟凛给白烬递了个安心的眼神。
王禁之没有回话,听孟凛茶壶落桌的声音,觉得心间仿佛有些发紧。
“十多年了,师父,往事一去不返,唯有世间人还在。”孟凛轻飘飘地落了座,“师父从前关心朝廷动向,却是不知我在朝中已然身陨的消息,既是不关心了,就以为师父已经放下就此隐居,不想心中还是有所顾忌,我全凭猜测,不想不知道真相而随意冤枉了好人,师父不愿说,那就听我来猜。”
“当年白将军一家身死,师父可知道……”孟凛缓声道:“他们是受了冤屈。”
王禁之再不碰孟凛倒的茶,他仿佛呆坐,不带一点情绪,“陈年往事,我都不记得了。”
“那就不说白将军。”孟凛耐着性子道:“说说师父你自己,当年师父医术在太医院一骑绝尘,不论是今上还是先帝,都时常召见您去侍候,师父在朝廷已久,恩宠荣华数不胜数,却是一朝避之不及,师父从前逼我还药钱的时候也并非视金钱如粪土的模样,却不得不离开,既不为财,徒儿斗胆一猜,乃是为了保命。”
“所以师父……”孟凛看着王禁之的脸色变化,“有什么不得不走的理由,逼得你一定要隐姓埋名呢?难道是……”
孟凛笑意收进一字一句里:“知道了些什么宫中人不可外传的秘密。”
此前孟凛向赵永佺求证,白家与宁家皆是知道了齐恂的把柄才招致杀身之祸,而算着当年王禁之离开朝廷的时间,大概也是那个时候,他对朝堂避之不及惹人猜疑,孟凛竟是将其联想到了一起,哪怕是猜测呢?
王禁之年纪已经大了,他往上摸了一把花白的头发,离京十几年,曾经一手带大的弟子也已经成了独当一面的太医,面前治病的儿郎也不像当初花言巧语的少年,他叹声道:“我知道些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往事挥之如炬,我不想再多加提及。”
孟凛沉默了些许,又道:“师父,我可是去查过你从前出诊的名册……”
“孟凛。”王禁之稍微厉声打断了他,“你莫要诓我了,从前的名册早就毁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王禁之说完了又偏头回想了会儿,他从怀里掏出那方才写的药方递了出去,“这药方你拿着,你也别为难我了。”
孟凛还想开口,却对上了白烬的表情,他竟是对孟凛细微地摇了摇头,孟凛将那药方收了,“也罢,多谢师父诊治。”
他与白烬对视着起身,“师父难以放下心结我自然不应当强求,但这些日子,就还麻烦师父在江家多待些时日,江家绝不亏待,连带往日欠的用药银钱,也自当一并补上。”
王禁之呆坐在原地,他望着孟凛与白烬起身的方向看了一眼,神色复杂。
快到门边,白烬忽然回过头,正正就对上了王禁之望过来的视线。
白烬的一丝忧色藏得有些拙略,“孟凛叫您一句师父,我也一向敬重您。”
“王大夫,您可曾想过,我为何也姓白。”
房门“嘎吱”一声闭上,王禁之瞳孔不禁一震,白烬方才说……他也姓白……
难道他是……
作话:
然后孟凛就开始吃药和补身子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