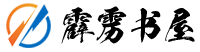如此一番折腾,艳阳当空,时辰已经不早。
白烬留吴常在旁照顾孟凛,一宿没怎么闭眼的林净山靠在榻上小憩,白烬又吩咐了林归回一趟六王府,让他去看六殿下的情况。
然后白烬言出必行,他让楼远跟着,与方扶风一道回了东宫。
可齐恂并未见白烬,他只见了一面方扶风。
太子殿下面露不悦,“你怎么把他给带回来了。”
方扶风也无可奈何,“白小将军性子执拗,此事定然是要追根究底。”
“追根究底就让他去查。”齐恂昨夜去萧府费了心神,他揉着眉心,“刑部那边拿了本宫的口谕,这事已经交由你了,白烬如何查你去跟着,不必让他来见我了。”
方扶风领旨退了出去。
查案便去了刑部。
如今唯一的缺口就是那个招认孟凛的内宦,他并非御膳房的人,而是安排在御花园引路的小太监,其中接触御膳房点心的时间也不过在送点心的路上。
刑部大牢在艳阳天里依旧晦暗,仿佛还郁积着冬日里的严寒,肃杀与血腥的味道弥漫不去,让人走在其间像落了地狱。
大牢的狱卒在前面引着路,身后跟着方大人、白小将军和楼少将军,他几乎要把腰弯到了地上,“几位大人将军这边请。”
“太监嘛,嘴上哪有把门的,又细皮嫩肉,才进大牢打了几棒杀威棒,就什么都招了。”
“诶当然,小人什么都没说出去,不敢胡言乱语,不敢胡言乱语……”
那狱卒卑躬屈膝地一路赔笑,却是没换来一个好脸色,只好悻悻地把嘴闭上了。
白烬已经许久没有来过刑部大牢了,经过牢房耳畔响动着锁链的声音,又是这般阴郁的味道刺激着鼻息,他从前来这里……审问过孟凛。
那记忆实在太坏了,上一世孟凛死在刑部大牢里,因而这一次他无论如何,也不要让孟凛同刑部大牢再有一丁点的瓜葛。
白烬几人在审讯室里等候,狱卒早先给白烬递了供词过去,他还在翻着,看得愈发神色凝重。
一会儿几个狱卒拖了个太监过来,那太监被剥去了太监服,白色的里衣已经横上了血迹和污垢,狼狈极了。
狱卒把他丢到地上,一个人顺势就踢了他一脚,“常青,还不快起来给各位的大人行礼!”
那太监常青还没反应,白烬先是冷眉点了面前的狱卒,“你们先退下。”
几个狱卒面面相觑,不敢在一群大人面前造次,乖顺地退了出去。
常青趴在地上大口喘着气,他受了刑,惊恐的眼神朝面前的人扫了一圈,扶地锁链乱晃,费力地跪在地上磕了个头。
方扶风眼神轻蔑,他后背靠着桌子,“常青,你跟白小将军说说,你都招认了什么?”
常青被白烬冷厉的眼神戳得后背发凉,他语无伦次地继续磕头,“是我……是我在御膳房的点心里下了毒……是……是孟大人……孟大人让我给……”
“谁?”白烬一声冷语骤然打断了他,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常青,“你重说一遍。”
常青愕然一愣,他嘴巴颤巍地上下不合,方扶风看着场面插了话来,“白烬,没有你这般恐吓的道理。”
楼远正给白烬挪了个椅子过来坐下,白烬缓了些语气:“常青,你平日在御花园当差,过得并不顺心吗?”
常青不想他会问这个,胆怯地不知如何作答,“不……不曾……”
白烬捏着供词,“那你这供词倒写得荒唐。”
“你替六殿下从御膳房取了点心,便在回御花园的路上在其中糕点下了毒药,你又并非日子过得不顺心,为何要做这等自毁来日的傻事?”
“我……奴才……”常青仿佛也是想及来日,闭眼就滴了眼泪出来,“奴才是受了人指使……才……”
“受孟大人指使?”白烬语气又不自觉冷了下来,“你和他见过几次,他让你豁出性命,你为了五十两银子,就敢给六殿下和萧家小姐下毒?他们若是因此出了人命,你可知会有多少人因此而死,你家中亲友、御花园数名内侍,无一能逃脱罪罚。”
常青的脸倏然惨白,他抖动着手又是往地上磕头,“他……他跟我说那药不过是泻药,孟大人说他不欲同萧家小姐成婚,只想让她身子不适早些离去,奴才……奴才真不知道那是毒药啊!奴才怎么敢谋害六殿下……”
“小将军,小将军……”常青抬起头时几乎是涕泗横流,他又抓着锁链跪着往前挪了两步,不想楼远横刀就拦在前面,他呆愣愣地停下,“奴才……奴才……”
常青咬着下唇几乎要出血,他眼神在面前的人里晃悠,却又没再说了。
白烬又翻了遍供词,他的话说得同供词一致,可孟凛要想下毒,他手下大有人去偷偷下手,并不会找个能查到又嘴不严的太监来办,而且白烬前两日与孟凛同去同归,孟凛又与他坦明过立场,现今这场面他做不出这样的事。
况且……孟凛如今哪里来的五十两银子……
白烬示意楼远把刀拿开,“单单五十两银子就能买你,你很缺钱吗?”
“我……”常青捏着手里冰冷的锁链,他垂泪道:“我母亲……母亲病了,我……”
“母亲病了就敢大逆不道。”方扶风冷不丁地插了话来,“病急乱投医,只会害了你自己。”
“方大人。”楼远看白烬脸上露出不悦,立刻白了方扶风一眼,“你不妨出去?白小将军不喜欢听你说话。”
“……”楼远还怪实诚,白烬偏首道:“如此也好。”
方扶风从桌上靠起,他有些怒道:“你二人沆瀣一气,是不是想借此机会私相授受,替孟凛脱罪?”
“你凶什么?”楼远瞅着他,“方扶风,是不是方才跟你没打出胜负吵闹,你还想再跟我再打一次?”
“楼远!”方扶风恼怒地同他争吵起来……
借着耳边吵闹,白烬面对着常青,常青刚往前挪的那两步已经离他近了,白烬连着嘴型,声音放低了些:“你不信我?”
常青手间一紧,又是惊慌地把眼睛别开了。
这内宦方才对着白烬有些欲言又止的模样,似乎是有什么内情想跟他说,可又心中纠结,这才作出有口难言的样子,他母亲病了……白烬大概猜来,怕是有人在他母亲身上做了文章。
白烬来京城已经有半年多了,他虽然不是自吹自擂之人,却凡事还能自诩些公道,除开在孟凛这里开了挂念私情的先河,京城里……不平之事甚多,却也许多人知道他公正的名声,何况这个宫中当差的人。
常青攥手掐着自己,他嘴巴上下翕张,“奴……奴才不知会是将军您来审理……可是……可是……”
常青仿佛崩溃地哭了起来,他哭至一半,喉中忽地哽咽,白烬倏地眼角一跳,他赶紧上前两指点到他的穴位,又是一下掐住了他的下颌,常青一声咳响,嘴中吐了口血出来。
“咬舌自尽……”楼远顾不得跟方扶风吵嚷,他赶紧上去一齐按住了常青,又对方扶风吼道:“我说方大人,你快去叫人啊,最好喊个大夫过来!”
“你……”方扶风瞪了他一眼,却还是移着步子出去了。
常青嘴角涌着鲜血,他眼看着方扶风出去,才小声地到白烬耳边,“小……小将军,我母亲……我母亲遭人绑架,我不得已……才……”
“我,我贱命一条,可我母亲受尽磨难……”常青自行擦着血,“小将军,求您……”
白烬手指探往他的喉间,“到底是谁让你投了毒?”
常青脑子里飞快地闪过些画面——前一夜他刚要从御花园中离去,却是突然身后一阵剧痛没了神志,醒来就被塞着嘴五花大绑地关在个阴暗的房间里,他惊慌之际听到外面的人声:
“事情办妥了吗?”
“人已经关到金乐坊里了……”
外头又悄声说了会儿话,这房间的门就被推开了,常青身子一抖,看着一人蒙着面从外面进来。
那人径直走到常青面前,当着他惊慌失措的眼,往他脚步扔了个木簪子过去。
常青的眼睛骤然圆瞪,他咬着牙间的布团,费力地挣扎起来。
“小公公。”面前的蒙面人细声地对他道:“若想这簪子的主人无事,你须得帮我办件事情。”
………
常青想起事情就情绪激动,“我,我也不认……啊……”
听着一点动静常青都像是惊弓之鸟,门口方扶风的脚步踩得他心底一颤,任何一个呆在宫中的人他都不敢相信,他只得快速地在白烬耳边说了句:“去,去金乐坊……”
鱼贯而入的狱卒进门被这场面一时吓着,恐是惊扰了里头的将军,白烬刚一站起身来,立马就拖着常青查看着嘴中。
“还好,还好。”狱卒讨好地凑到白烬跟前,“小将军,这人还没死,还能审,还能审。”
白烬却是退了步,“把人押回去,午后我再过来,莫要让人死了。”
“是是是。”狱卒得了命令就把人往外拖。
“小将军。”方扶风靠在门边仿佛看戏,“今日已经过了半日,太子殿下顾念些表面情分暂时未曾公开,这事却怎么也是刺杀毒害的大事,你家六殿下至今没有醒来,如今人证物证俱在,怎么你却一心顾念着给你家那个开脱?”
“其中疑点尚未明晰。”白烬折叠起供词给楼远拿着,“方大人结案之心未免太过着急了。”
“我急什么?这事儿和东宫可挨不着边,刀都是别人递的,怕是你不知道,孟凛都和什么人有过过节。”方扶风眉梢一挑,“你别忘了,我们殿下本是要和孟凛当亲家的。”
白烬的确是怀疑这事和东宫有关系,可萧家小姐的确是齐恂的妹妹,太子一党本是要拉拢孟凛的,如今怎么会又来陷害于他,难道是拉拢不成……可这手下得似乎过于快了。
这审讯室里只有一扇小窗,外头的明媚只能漏进来一点,正正照在了白烬站的位置,他往窗外看了眼,“方大人,午时了。”
“怎么?”方扶风道:“小将军还要请我吃饭?”
“没错。”白烬从那日影下走出来,“是要请方大人吃饭。”
***
将军府。
林净山打了个盹的功夫,孟凛就醒了过来。
孟凛醒来顿觉喉中一片腥甜,比他平日里病发时更觉得难受了,他咳了两声还是有些后悔,这法子以后还是少用为好。
吴常立即凑了过去,“公子。”
“常叔。”孟凛哑声问:“白烬呢?”
吴常扶着他的动作坐起来,“白烬去了东宫,查……你的案子。”
孟凛苦笑了句,“常叔,我又没做什么坏事。”
“孟大人。”林净山听着动静走过来。
孟凛虚弱地朝他点头道:“林太医……有劳你了。”
“举手之劳。”林净山再去给孟凛把脉,“孟大人,你身子本就虚弱,这番实在不应当剑走偏锋啊。”
看来林净山是看出了他吃药的事情,孟凛捂着胸口咳嗽,“林太医,我这番才刚刚入仕,又未同旁人结仇,不想就遭了陷害,出此下策实乃无奈之举。”
他一脸神伤,“实在是听闻刑部严苛,我若进去,怕是连那几棒杀威棒都挨不住,若不这般自保一番,怕是就与……咳,与白小将军天人相隔了。”
“……”林净山欲言又止,只好道:“能看出你与白小将军私交甚笃。”
孟凛手间一颤,忍不住又咳了声,从前听旁人说起他们私交甚笃,他还当是个吉利话同人开心玩笑,可如今……如今经过了昨日的事情,孟凛忽地有些心中五味陈杂了。
林净山见他出神,接过了话去,“孟大人,在下有一事相问。”
孟凛抬手道:“太医为我诊治当为大恩,在下定然知无不言。”
“在下自小入太医院学医,如今已历经二十载,承蒙陛下厚爱,怜惜我的医术,旁人也尊崇家师,愿以前任院判之徒的名声加之于我,每每听此,我总会自省,是否有愧师父教授医术,未能扬其威名。”说及师父,林净山揖手向侧,话里带着敬意。
孟凛与他正色道:“林太医宅心仁厚,医术精湛,当配得上师传美名。”
“既然如此。”林净山偏首视着孟凛,“孟大人可知家师的名号。”
“愿闻其详。”
“家师为前任太医院院判——林示。”林净山注视着孟凛的表情,“在下性子急,不喜弯弯绕绕,因此同你直言,孟大人自保,这事在朝中当属寻常,我一介太医,并不愿牵扯其中,但是孟大人所食之药……”
林净山紧了紧手,“在下觉得,似曾相识。”
孟凛同林净山相视了片刻,他忽地低头笑了声,“当真是瞒不过你……”
“师兄。”
作话:
呜呜呜最近工作有点忙下午没能更新,这才拖到了晚上,还好今天还没过去!
明天周末快乐~
所有人都要知道小将军和新科状元交情不浅了
关于师父是太医院院判的伏笔:应如晦受伤那次喝了孟凛的药,和他打趣,“孟公子开的药好苦,让我想起幼时喝过太医院的药,也是这般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