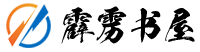楼远留守京中,替白烬在京城里留了一双眼睛。
孟凛一目十行地读过去,那信里大致是说,归州城破的消息传到京城,建昭帝就迎民心所向,亲自摆驾去了城外陀安寺上香,为前线将士祈福,此行是由北衙禁军的统帅楼怀钦楼大将军亲自护卫,几乎将寺庙围成了铁桶,但陛下在寺中停留的第二日,竟然凭空失了踪迹。
巧合至此,当天下午太子齐恂就去寺中求见父皇,楼大将军还没来得及将寺庙翻过来,就获罪了失职之责,太子的口谕,暂时撤了楼怀钦的大将军之职,他的人也如神兵天降,当即过来接管了禁军。
而这事情发生没两日,太子手下的侍卫亲军就在陀安寺后山的山林找到了建昭皇帝,可不知是何人动手,陛下竟然昏迷不醒,太医诊治是为中毒。
这事情发生得太快,还没给齐曜和齐越反应过来,齐恂就已经把陛下护送回京了,因为早先护卫不力,建昭帝身边的护卫给换了彻底,甚至是换上了齐恂的人。
而后就是四皇子齐越与六皇子齐曜一同受旨入宫侍疾,连同太子齐恂,三个人的消息,几乎都被隔离在了皇宫之中。
孟凛明白了白烬表情凝重的缘由,他把手缓缓垂下,“当初齐恂引你出京南下,怕就是早预备了这一出了,京中失守,他才好开始动作。”
白烬好像并不想多说,他从孟凛手里把信拿过去,又走到灯烛边开始把信纸燃了,“我……”
他心中似在纠结,“我再想想。”
白烬将信纸点燃,又处理了灰烬,这片刻的光景他好像把方才的烦忧都拭去了,他又重新走到孟凛身侧,望了望天色,“午时将至,今日你想吃点什么?”
孟凛的伤还没好,日日都还躺着坐着,他的日常起居都是白烬在照看,近乎于无微不至了,孟凛仰头回应着笑道:“小公子做什么我都爱吃,随意做些就好。”
“好。”白烬拭了拭手,“等我回来。”
孟凛看着白烬转身离去,他方才脸上的笑意才渐渐消失,“京城……”
京城里出事了,以白烬的身份性子,他不可能会不在意,但他却要在孟凛面前回归平常地不再提及,孟凛心里其实很不是滋味。
如今南朝大军的攻势如何他并不得知,但近来白烬离开的次数越来越多,孟凛如何也能猜出情况并不乐观,可他如今伤势未好,白烬每日都变着法子来围着他转,方才他看到京城里的变故,恐怕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他若离去,前线的战事与孟凛该如何安放的事宜。
孟凛有那么一刻自问:“我是他的累赘吗?”
他失望地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心里好像是下了什么决心。
午后孟凛同白烬说他要休息,白烬就暂且离去,留了孟凛一人在房中,但孟凛偷偷唤了人,把江桓叫过来了。
江桓过来还在挖苦孟凛,“怎么不让白烬陪你,喊我过来做什么?”
孟凛却摇了摇头,让他先别与自己贫嘴,江桓一怔,他忽而发现这些天过得舒适放松的孟凛,好像忽然正经起来,孟凛靠在床上,侧首问道:“这些日子,外面的动静我未曾过问,现在是什么情况?”
“唔……”江桓好像有些为难,他离了几步站着,“白烬他,他不让我说……尤其,尤其他今日又跟我提了一趟。”
孟凛心说白烬实在太了解自己,但他又执拗地望着江桓,“你知道你不同我说,我也有法子知道的。”
江桓在视线里对峙,最终还是缴械投降了,“就是,就是南朝那些人不知道是不是有病,非要打着救出主帅的旗号,竟然又冲过来要攻城,就算是朱启明死了,也要把那个孟……孟什么的世子救回去,还有,还有你。”
“孟阳……”孟凛这些日子不问因果,什么都没管过,“孟阳如今怎么样了?”
“就关着呗。”江桓不屑道:“那人白烬好像认识,说是你也没说要取他性命,就把人一直都关着。”
孟凛不置可否,“这些时日只要他不在南朝出现,他的命留着与否,也不重要了。”
“那……那个孟隐呢?”江桓好像眼底都晦暗了些,“这些日子不敢烦你,你又没提,所以人还留着,等着你发话。”他话里怀疑,“你不会真……尽释前嫌吧?”
“尽释前嫌?”孟凛觉得自己伤口隐隐痛了下,眼里的冷意更明显了,“我岂是那般好心的。”
他把目光落在自己的右手上,话里很是淡漠,“把人活剐了,人死了就把头割下来,给孟明枢送回去。”
江桓并不觉得意外,“好。”
“除此之外……”孟凛低垂的目光并未抬起,他是停顿了才道:“你再帮我做两件事。”
江桓洗耳恭听,就见孟凛直起身好似是要起来,江桓赶紧过去扶了他,孟凛一边道:“你替我写封信送往岭中,然后……”
“我也该去做我未曾做完的事了。”
……
第二日夜中,归州城动乱,北门不知为何从城中破开,好似是撕开了一条口子,此前被北朝军队抓获的南朝兵士竟簇拥着一辆马车突击至此,从那北门连夜奔逃出去。
马车与兵士直奔了南朝将士驻扎的营地,那一夜营地灯火通明了一整宿。
而在晨光熹微之时,归州城楼上有个独自上楼的影子,眺望着南朝的方向。
孟凛走了……昨夜江桓引他离开的时候白烬并未多想,他以为江桓至少不会送孟凛进入险境,可孟凛竟然带着江桓一道走了。
他带走了江家的护卫,带走了城中关押的孟阳的护卫与南朝的将士,还带走了朱启明的尸首。
分明昨日是不该给他看到朝廷里来的密信的,只是事关齐恂,白烬不想瞒着他,如今朝中生变,白烬却远在千里,他的手如何也伸不了那么远,但是如果他此时回朝,南朝的大军就无人抵御,孟凛伤势还未好他不想离开他的身侧,因而白烬还在为此纠结。
他没有想到孟凛的决心会下得这么快。
天边的晨阳愈来愈亮,又一个人影也上了城楼,应如晦站在白烬身后,他话里好似有些埋怨,“你家孟公子不讲武德,他一心赴险,竟然连带着把江桓也带走了。”
白烬回头看了一眼,“他们倒是兄弟同心。”
“那白将军如今如何打算?”应如晦站在白烬身侧,“你眼前的障碍扫除,也该有所抉择了。”
白烬什么也没说,他只转过身,对向了北朝的方向。
北朝京都长安。
现如今京城戒严,尤其是皇宫之内,日夜都有人巡视周围,三位皇子已经许些日子没有出宫了。
建昭帝的寝殿殿门紧闭,殿里视线昏暗,灯烛上套了层遮光的烛罩,入眼的烛光显得柔和了许多,但里头的气氛很是沉重。
皇帝尚且还在昏迷,正有内侍给建昭帝喂着汤药,齐恂隔了几步站在一旁,身侧跪着太医林净山。
“林太医。”齐恂睨了他一眼,“父皇如今情况如何?”
林净山伏着头,“下官,下官已是尽力,但陛下所中之毒不知来源,解毒怕是还需时日……”
“林太医的意思就是没有法子了?”齐恂望着床上,“你于太医院名声甚好,父皇也一向信任你,但是如果治不回父皇……你知道下场。”
建昭帝回宫多久,林净山就已经医治了多少时日,可他并非神医,这些日子被关在皇宫里,他已经是尽力了,但治不好陛下,等着林净山的就是死罪,他摸了下额头上的冷汗,“殿下明鉴,下官再试试,再试试……”
齐恂走过去看了眼建昭皇帝的模样,中毒多日,原本就已经年迈的建昭帝眼窝深陷,深色的唇上颜色不褪,整个人憔悴了不是半点,竟显了风烛残年的老态。
齐恂那低垂的眸子扫了几眼,却深沉得不带情绪,他转身就从寝殿里出去。
门口就是他的身边侍卫亲军的谢化在候着,他朝齐恂行了礼,“殿下。”
随着身后寝殿的门阖上,齐恂偏身等着他的后话,“何事?”
谢化朝齐恂走近了步,低了声音道:“这些日子人都调来了皇宫,东宫戒备就……昨日竟然遭人闯进,此前抓到那个女人,被人救走了。”
“白烬身边那个暗卫的妻?”齐恂眯了眯眼,但他好像不甚在意,“从前抓了她,也只是想牵制一下白烬,如今他远在南朝,人没了就没了,不过现如今还会做这事的,想必就是楼远了。”
“本宫撤了他父亲的职,他对我心里生怨也是寻常,何况头一回还是在他手里抢走了人,但他势单力薄,不用管他。”齐恂把视线转向一旁的宫殿,“那里面的两位呢?”
“六皇子倒是安分,只是说过几次要见陛下,但想来他知道自己处境,也就没有再闹了,就是三皇子……”谢化好像有些为难,“三皇子出身矜贵,想来是受不了软禁,说是要见他府上的夫人。”
如今皇宫在齐恂的掌握之中,齐曜和齐越一进宫,几乎就遭了软禁,这事的消息被齐恂垄断,宫外几乎得不到消息。
齐恂皱了皱眉,但他通晓齐越的脾气秉性,犹豫了片刻,“他要找的是那个秋筠?”
等谢化点了头,齐恂无奈道:“那就把那个女子宣进宫,让她陪着,省得齐越坏了我的大事。”
“齐曜身边的人还没有什么动作吗?”齐恂理了理自己的衣袖,“他若是一直如此沉得住气,届时等到林净山束手无策,就算是为时已晚,但他若现在动作,以他六王府的那些人,只能算是螳臂当车。”
谢化道:“属下一直注意六王府的动向,但近日时常出入的……只有六王妃。”
“阿锦?”齐恂眉头一皱,“阿锦对齐曜一片真心,可她一个女子……罢了,让人去把萧仪锦接去姑母身边住上一段日子,省得她做些什么傻事,但她在宫里就让她呆好了,莫要让她去见齐曜。”
“是。”等齐恂没了别的吩咐,谢化领了旨就已离去。
齐恂在宫殿门口站立,他往眼前一望,皇帝的寝宫立于台阶之上,往下就能望见宫中的诸多屋檐,偌大的皇宫之中,竟显得齐恂的身影渺小了许多。
但齐恂知道自己离大计只有一步之遥。
当日下午,接人的马车就从宫里去了六王府。
萧仪锦听闻了消息并未惊讶,她让人稍微收拾了行李,就跟着过来的人上了马车。
即便萧仪锦嫁了六皇子,但她依旧唤得太子殿下一声表兄,来人自然不敢为难她,她又为人亲厚,对来人没有旁的要求,只在身边带了两个侍女。
那两个侍女都跟着萧仪锦坐上马车,马车缓缓行驶,朝着皇宫去了。
马车上两个侍女与萧仪锦相对而坐,却都戴了面纱,萧仪锦朝二人看了一会儿,忍不住露出了一点笑声。
其中一人无奈道:“王妃娘娘,您就别笑话了。”
那声音竟是个男子,那若隐若现的面纱下面,妆面厚重得看不出模样,但这声音听着像是楼远。
萧仪锦掩了掩嘴,“从前与少将军也算是见过许多面,倒真没见过少将军女装的样子,不知道楼大将军见了是何反应。”
“可不能让我爹看见。”楼远隔着面纱给自己扇了扇风,“这不是没有办法,若是以护卫身份,进宫可就没这么容易,是吧?”
楼远朝旁边那“侍女”道:“陈羽。”
陈羽有些局促,他养好了伤,终于回京与楼远一道夺回了发妻,如今京城生变,他没法置身事外地这时候离开,就跟着楼远一道混入皇宫,他木讷地“嗯”了一声。
“但此行有些危险。”萧仪锦除却笑意,还是有些担心道:“我不过是去面见姑母,想必太子表哥是不会让我见到殿下的,到时候……可能就要倚靠你们了。”
“其实……”楼远话里有些歉意,“其实我明明知道你与太子的关系,还让你来带我们进宫,本是不合道理。”
萧仪锦却垂眸苦笑了下,“无妨……此事早在许久之前,我就已做了承诺。”
她想起未能如愿嫁给齐曜之前,曾经被白烬与孟凛直接问道:“来日你的太子表哥与六殿下只能有一人得势,你会选谁?”
萧仪锦也记得自己当时的答案:“来日若是真要选择,我信天理道义,抉择……公理之辈。”
马车摇晃不久,就已到了宫门。
那马车不能进宫,因而停在了宫门,萧仪锦和她的侍女从马车上下来,验好了携带之物,就有了萧贵妃宫里的内侍过来接人。
萧仪锦身份尊贵,在宫中时常走动,宫门的侍卫与内侍都认识她,因而这一行走得很是顺利,只是从宫门离去之时,有一侍卫看着两个侍女有些疑惑道:“今日王妃娘娘怎的没让身边的夏栀姑娘一起过来?”
萧仪锦端着大小姐的端方,她从容地笑道:“劳烦侍卫大哥关照,夏栀近来身子不适,但我许久不曾入宫,想着给姑母备些礼,因而带了两个姑娘一道进宫,敢问大哥可是有何不妥?”
“不敢不敢。”那侍卫赶紧退了一步,“王妃请。”
那萧贵妃宫里的内侍与一个同来的侍卫带着萧仪锦三人往后宫走,内侍低头走在前头,那侍卫好似带了警惕之心,他亦步亦趋走在后面,手却没有离开过腰间佩刀。
快到御花园时,萧仪锦忽而脚步一顿,“遭了。”
她转身时脸色好似有些着急,“方才从马车上下来有些着急,忘了将要给姑母的礼品拿上,这可如何是好?”
那侍卫怔了下,“不妨卑职带着王妃回去?”
“此去路远。”萧仪锦露了些疲惫的神情,“我让我的侍女与你去如何?我可先行去找姑母,或者你若是不放心,我也可以在此处等你。”
“这……”那侍卫有些犹豫,却见萧仪锦已经朝侍女使了颜色,只好道:“那劳烦王妃在此处稍候,卑职去去就来。”
萧仪锦话间和气,“也好。”
然而那侍卫转身之际,几乎同时,陈羽与楼远的手就伸向了那内侍和侍卫,不过颈后一击,两人就晕了过去。
楼远接住那侍卫倒下的身体,“王妃娘娘干得漂亮。”
萧仪锦呼了口气,“方才真是吓死我了,我可是从未做过如此失格之事。”
“萧小姐英勇无畏。”楼远拉着那侍卫就要进花丛,“楼远佩服,就是还劳烦王妃娘娘帮忙照看一下来人,我们,我们也好换个衣服。”
萧仪锦慌忙转身,不消片刻,楼远和陈羽换上了那内侍与侍卫的衣服。
两个人互相比照看了看,陈羽不禁皱眉,“我为何要穿太监的衣服。”
楼远噗嗤一笑,“没有办法,就来了这么两个人,何况太监更好行事,你可是赚了。”
陈羽不听他胡扯,直接问:“今日要如何行事?”
楼远也不多玩笑,“宫外安排了人里应外合,今夜最好能先把六殿下给救出来。”
“殿下……”萧仪锦本还要先行去往后宫,却停顿了一瞬,“我是否也能去面见殿下?”
“这……”楼远犹豫,“此时……怕不是好时机。”
萧仪锦低头抿了下嘴,但再抬首时眼神坚定:“楼少将军,其实,我心中还有一计。”
……
这日宫外,也不知从何处传来,忽而有一论调甚嚣尘上。
“如今这宫中是何人主事?”一书生打扮的人在茶馆中与旁人谈论,“陛下?”
那人摇了摇头,“陛下从城外陀安寺里回来,就一病不起,如今几位皇子都在宫中侍疾,但这么些时日都还没有消息传出,看来京城里啊,是要变天!”
“陛下本来还未有沉疴入骨的征兆,怎么如今就……”旁边一个年轻人怀疑道:“这其中似乎有些蹊跷。”
“如今连前朝就有的楼大将军都被罢了职,想必陀安寺中必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但是其中内情……”那书生似乎讳莫如深,“当日护卫与带入京城的,都是当今太子殿下,其中内情想必也只有太子可知了。”
“这……”身旁人都有些惶恐,“兄台慎言……”
太子殿下前去护卫,又带了陛下回宫,中间的内情除了当今陛下,当然也只有太子知道,但是事情若如此说来,仿佛言外之意,还能让人联想到建昭皇帝的病也与他有所关联。
“是是是……”那人小声道:“但话虽如此,这宫中的侍卫其实都已换上了太子的人,谁人主事……其实也不算什么秘闻了。”
几人谈话之后就已散开,那茶馆中却是有人立起耳朵听着动静,楼上雅间的门被缓缓推开,有一店家小二身份的人提着茶水进了雅间。
里头有个人好似悠闲惬意地喝着茶,那店小二擦着桌子去给他添了一杯茶水,凑近之时压了声音道:“大人,话都传出去了。”
那人慢悠悠的端起茶杯,“知道了。”
他透过窗户看向外面,这京都底下的风起云涌好像也如表面一样繁华,这人正是礼部尚书,应于渚。
不过一日,城中竟有泼天的传言,说是太子殿下已然占据宫闱,当日寺中之事,或还与他有着莫大关系,更有传出去的谣言,说是齐恂登位在即,却是他使了计谋,如今陛下卧病在床,就是他所行不轨。
真假不辨的谣言如同大网忽然笼罩了京城,等到齐恂属下回禀,已然是蔚然成风。
事情的发展犹如飞出的羽箭,那夜因为城中流言提早宵禁,夜里的街道,却有马蹄与刀剑的声响。
一支并并未带有统一标志的兵士四散在了城中,他们所骑的马来源不一,禁军麾下羽林军、龙骧军甚至还有侍卫亲军的装束,这些分散的兵士好像并无目的,只绕着整座皇城来回绕着圈子,哒哒的马蹄好像夜里的暗影在城中肆虐,仿佛要把这动静弄得全城皆知。
紧紧闭上的窗子忍不住探出口来,今日方才得知流言的民众竟是将其混为一谈,或是今夜,就是长安城要变天的时候。
宫里很快就注意到了城中的动静,城中禁军立刻就派了人出来,却使得城里更像是兵马动乱。
待大街之上,禁军人马分散开来将人堵住,兵马刀兵相向之际,却发现街上之人均为同营的兄弟。
领兵的将领不知情况,对着本营的兵士发问:“为何叛乱!”
“不为叛乱。”一将士扬起大刀,掀起自己装束的衣袍,挥刀就割下了一片衣角,“是为救主!”
“你们为的什么主!”那将领怒斥之下,忍不住道:“十多年的兄弟,今夜怎可聚众叛乱!”
“十多年的兄弟……”那将士仰天看了一眼,“十多年前,我等还并非禁军麾下,我等忠于……”
那些将士几乎一字一句:“白家将门。”
几乎一样的夜晚,京城之中,十多年前一心忠君爱国的白延章白大将军一朝获罪,其下领兵的几万大军,要么一道领罪,要么被并入其他营内,从前将门白家不复,那经营多年的常胜大军,一夜就失了爪牙。
“白大将军忠君爱国,却被齐恂诬陷,一夜成了叛乱之辈,如今眼看太子夺权,那就是昭雪无望!”一将士挥起大刀,“我等身为下属,却苟延残喘多年,是为不忠,故而今夜不为叛乱,是为救主!”
白大将军已经成了历史的尘埃,叛国的罪名使得无人敢多加提起他的名字,可当初他麾下的众多将士,跟着白家一道北上征战,一道入城救主,其中的忠奸与否外人听信流言,自己人却看得明白,如今多年过去,世人以为当初白家依然没入往事无人再会提起,可他将门之中,依旧是有数名将士,依旧记得当年的荣光。
历史洗不清白家的世代忠名。
“放肆!”那将领气急,“今夜只要在城中伤人,那就是叛乱!你们如今穿着我军衣甲,是要拉我等一同下水吗?”
“那就得罪——”挥舞的大刀映上城中举起的火把,刀剑的冷光在城中乱晃,但那些四散的兵士却并没有殊死一战的模样,而是四下逃窜,仿佛只为了将城中搅乱。
禁军不得已也分散开来,将整个京城的街道围了满城,城中的热闹仿佛与白日可比,却是充满了刀光凛凛的影子。
作话:
应该还有两章就完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