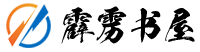烛火摇曳,已是入夜时分。
应如晦走到孟凛窗前,看到了他被烛光照出的大致轮廓,心里忽而有些复杂——他和孟凛从前的恩怨说不分明,自己起过利用的心,孟凛更是没把他的性命当回事过,可如今他站在此处,知晓了孟凛的出身背景,心里竟然少见地生出了几分怜悯,即便他知道孟凛并不需要。
“孟公子。”应如晦敲响了房门。
孟凛正坐在书桌旁放下笔,把几封写好的信收进了个锦盒里,他抬起头,“进。”
应如晦从外面进来,他轻声阖上门,“白日不便打扰,倒是夜里叨扰了。”
“应大人客气。”孟凛并未相迎,他挪开锦盒在书桌前坐正,“只是明日在下还有要事在身,无暇与应大人于唇舌之上多费功夫,既是应大人找我,不妨开门见山。”
“好。”应如晦拂了拂衣袖,视线正盯着孟凛平静的表情,“我听江桓说,你答应让他陪同你去南朝。”
孟凛收拾纸笔的手间一顿,“是,小桓担忧我的安危,想要陪同我一道回南朝。”
“不可。”应如晦皱起眉头来重复,“此事不可。”
“为何不可?”孟凛把手合着放在桌上,他好整以暇地抬首道:“难道应大人,愿意亲自陪我去南朝?”
应如晦的眉蹙得更深了,可他的话哽在了喉间,孟凛……还是从前那个孟凛。
他明明知道应如晦不可能将此事应承下来,应如晦一介朝廷命官,又出身世家,若他没有皇命私自前往南朝,定然逃不过一个通敌的罪名,此事一旦被人知晓,立刻就会有无数人戳着他的脊梁骨要将应家满门抄斩。
孟凛在应如晦的沉默中轻笑了声,“应如晦,你觉得我此次回南朝,是在送死?”
应如晦何时都能想出最妥帖的回法:“孟公子深谋远虑,足智多谋,应某自然希望你得偿所愿。”
这话实在太漂亮,孟凛笑着摇了摇头,“所以应大人还未回答,是否愿意替小桓承担此去南朝的诸般险阻。”
“孟凛。”应如晦盯着他的笑眼:“我力所能及之处,定然会尽力保全江桓的安危,可……你知道我去不了南朝,正如同白将军也不便参与其中。”
孟凛像是失望,笑意全消失在了嘴角,“如此就没得说了,我已交代了江家的诸位长老,岭中的事情自然会有人同你对接,至于江桓……”
应如晦把手撑在了桌上,他叹了口气,“你想试探于我,其实我大可说句愿意,由此打消你的疑虑,孟凛,你看江桓如此之重,我不信你会真的让他置身险境。”
“是吗?”灯烛下孟凛的脸变得柔和了些,可他眼底带了丝锋利,“你猜我会心软,但实际上,我本来的打算,就是想逼你同我一道去南朝,江桓早已不是稚子,其实早不必我来挂心,也用不着你来护卫。”
两人在寂静的空气里对峙,应如晦微眯的眼里映进了旁边烛火的火苗,他几乎要相信孟凛这话是认真的了。
“可惜了。”孟凛终于松口道:“他也舍不得你去涉险,我可以不顾惜你,却不得不顾惜他。”
孟凛眨眼间垂下了眼,“应如晦,你其实应当感谢一番白烬,我从前并没有如今这般心软。”
说到白烬,孟凛心里不可避免地动了下,因为白烬,他竟做惯了爱屋及乌的事,他乐意因为白烬而改变对世间的淡漠,或许只因与白烬相处时一缕阳光落在他的身畔,他忽然也想从那明媚里触及到这世间所有的风花雪月了。
晃动的烛火下,应如晦的眉心终于展开了,他从怀中掏出一个物什递到孟凛面前,“兄长此去艰险,我没有旁的东西相赠,或有一物,想给你……添些筹码。”
孟凛听到“兄长”,还是起了鸡皮疙瘩,可他看清那东西,略微有些惊讶,“应大人这是何意?”
那桌上放了一块赤红色的令牌,十分小巧,上头只有个“晖”字。
孟凛大致猜得出这令牌做何用处,六皇子齐曜身边的暗卫,唤作“晖影”。
应如晦收回手,“在孟公子心里,我此来岭中,不正是图谋不轨吗?”
“南北两朝皆有图谋,此事我心知肚明,你家殿下在南朝埋些暗线,的确不足为奇。”孟凛摸过那块小巧的令牌,“可把这东西交给我,应大人,你何时如此信任我了?”
应如晦眼里含了点笑,“从来是孟公子对我不轻易言信,我可是一开始就递了诚意,你我同朝为官也并非一日两日,为殿下做事也是你亲自应承,何况,白将军信你。”
“白烬信我……”孟凛心里柔软地念叨了句,连带眼里的锋芒也淡了,他淡淡道:“可我此去为了私仇,并非为了大义。”
应如晦从善如流道:“南朝的晖影已蛰伏多年,如何使用全系孟公子心中所想,应某绝无相逼的意思。”
孟凛心里不过踌躇了一会儿,没有白捡便宜不要的道理,他将令牌捏在手里,“如此多谢。”
再聊了一会儿,应如晦就要离去,孟凛在他转身的时候,终于温声添道:“应如晦,你好生对待江桓。”
应如晦浅笑着同他点了个头,“兄长放心。”
“……”孟凛还是不禁骂了一句,“下次再喊兄长我把你赶出去。”
关门声响起,孟凛摩挲着那块令牌,放进了衣袖里,他盘算了下时间,该是下一个人来的时候了。
不消一会儿,江桓推门进来了。
江桓少有地在孟凛面前收起炸毛的脾气,还耐心地给孟凛倒了杯茶递过去了。
“孟凛,你真,你真不要我陪你去南朝?”
孟凛深谙打消他这想法的办法,接手道:“我让你去了南朝,然后任由应如晦图谋我江家的家产吗?”
“……”这话的确比说担忧他安危好使,可江桓还是嘟囔道:“应如晦他不会做得这么过头。”
“应如晦我方才见过,不想说他。”孟凛心里即便是乱,却也捋出了头绪,他如今放不下的人屈指可数,在这情分上的弟弟面前软下了声音,“又要走,我很抱歉。”
江桓嘴角动了动,此刻动容实在太过矫情,可心里还是难受的,“你……记得保全自己。”
“我的安危你不必挂心。”孟凛安慰似地拍了拍江桓的肩,“孟明枢大费周章让我回去,决计不会让我轻易死了,他知道我心中不忿,却执意此刻让我去鸡蛋碰一碰石头,不可能只是想溜我玩些幼稚的把戏,暂且应当不会对我动手。”
“所以我不担心自己,但我有些担心你,担心……白烬。”
听到自己放在白烬前头,江桓也就不想和他计较许多,“你有什么事想交代我尽管说。”
“江家在你手里我很放心,我虽同应如晦从前有过节,却也承认他的靠谱,唯独……”孟凛眼里不自觉有些发涩,“唯独白烬一个人身在京城。”
孟凛尽量语气平和地说着:“常叔的事他理应还不知道,可常叔一样看着白烬长大,他若知道了,必定心中不忿,坐立难安,但他有要事在身,朝中有我与他必定要除却的敌人,是有虎狼在侧,我不愿他为此分神回来,因而当前,我不想让他得知此事,添上,添上我去南朝……”
孟凛觉得心口微微泛疼,他其实早答应了白烬不再不告而别,也不再置身险境,也知道以白烬的性子得知此事,必定不会拦他,可见到白烬伤心孟凛心中不忍,所以……
“所以有件事,我想交代于你。”孟凛拿过书桌上的锦盒,在江桓面前打开,“其中有三封信,前两封是本月写好了,打算寄给白烬的家书,而余下一封……是何时这事瞒不住他,再想你移交给他的,他看了信再想罚我骂我我都无话可说,可若他并未发现,随后几月的书信,我也会从南朝送来。”
孟凛将锦盒递交给江桓,“小桓,还请你帮了兄长这个忙。”
江桓觉得心里好生难受,再凶猛的人有了软肋,也能露出一副柔软的样子,孟凛同从前还是有了千差万别,如今此情此景,他并非不能理解孟凛对白烬的感情,再多的情谊偏颇也在孟凛的柔软面前偏过了称来,他一想,自己其实并没有非要给白烬脸色的偏见,恩恩怨怨,大多都是平日里强加上去的。
江桓收了锦盒,对着夜色里的孟凛答应了下来。
这一夜烛火长燃,星河遍野,江府的灯在天亮一刻才渐渐熄灭。
天光洒在江府高挂的白绫上,明艳的阳光驱不散丧葬的沉闷,随着送葬的队伍往城外去,一辆缓缓移动的马车,也从江府驶出,从上洛城门出去了。
这一次离开,孟凛没有带许多人,走得极其安静,他出门之后没有回望江天一色的家门,也没多看一眼岭中的山色,他依旧穿着一身素色的白衣,闭着眼,朝着南朝的方向去了。
而正是这一日,北朝京城的街道上人人喜乐,红绸挂了京都多半的高楼,鞭炮震响了半个长安,原是今日六皇子齐曜娶亲,要与萧家小姐喜结连理。
大红的花轿从天门街的正街走过,萧仪锦握着手里遮脸的团扇,外头喧嚣入耳,她竟还能听到心里扑通的心跳声,扇下她的脸略微嫣红,少女出嫁,嘴上是带着笑的。
替六皇子接亲的是白烬,白将军穿着官袍骑在马上,风神俊逸的面容惹人赞叹,路旁围绕了无数的京城百姓,和乐地看着这皇家的大场面。
驶在高楼下,上面忽然炸开了个花球,无数的花瓣从天上洒落,人们笑盈盈地往天上望着,伸手接住各色的花瓣,嘴里喜悦地欢呼着,然后街上又向起了此起彼伏的鞭炮声。
花车一路朝着六王府去了。
作话:
看着他们其实我有一种,“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
在接亲的路上,白烬大概是想过他与孟凛如何成婚的
# 南朝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