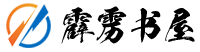岭中,江天一色。
是夜月圆,清辉洒向树梢檐角,落了满地虚影,江府庭院清幽,似是有人吩咐,把里面守着的人都撤了出去。
原来是江桓和应如晦在此赏月对饮。
江桓对月亮其实是不感兴趣的,那么大一个月亮盘子挂在天生,除了阴晴不定地发着光,也没什么好看的。
但是应如晦是个文人,听说文绉绉的人都喜欢对着月亮写诗,江桓翻了好几本写月亮的诗集出来,硬是读出好几分矫揉造作的鸡皮疙瘩,深觉这东西不大适合自己。
但他还是邀了应如晦过来赏月。
“咳咳。”江桓清了清嗓子,“应如晦,我这两天读了几篇,写月亮的诗,想……想跟你说道说道。”
“哦?”应如晦温柔地笑了笑,“愿闻其详。”
江桓摆了摆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应如晦捏着酒杯与江桓碰了一下,“如此心境,你可是想孟公子了?”
“嗯?”这跟孟凛有什么关系?江桓模棱两可地摸了摸鼻子,“大概吧,你这么一说,的确还是怪想他的。”
应如晦七窍玲珑,立刻明白了江桓对自己的良苦用心,他比照着月亮,“人生一世短之又短,世事多半瞬息万变,唯有明月千古不变,纵然阴晴圆缺,但始终高悬不曾坠落,因而古来就有许多人借着月亮畅抒情怀。”
他看了江桓一眼,“如此说可能有些过于晦涩,但是你想,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你要是去了远方举目无亲,认识的人都在千里之外,身边岂不是只有一个月亮看着同从前一样?所以古人多半用月亮寄托相思,就像此时,孟公子远在南朝,也能同你看到同一轮月亮。”
“唔……”江桓思索了会儿,“话是这么说,但除了月亮,太阳也是不变的,太阳还不像月亮那么反复无常,我和孟凛看到的太阳,应该也是同一个啊。”
“话是如此。”应如晦对江桓耐心笑着,“月亮阴晴圆缺,日日不同,正对应着人的悲欢离合,因而又有一些人,用着月亮来写人生际遇,所以月亮又有了旁的写法。”
江桓深觉这样的东西实在不适合自己,但是听应如晦耐心地给自己讲解,时间仿佛忽然给拉回了幼时在国子监读书的时候,那时应如晦也是耐心地给他讲书上的功课,即便自己一如既往地不感兴趣。
但他能给自己说,江桓心里也是开心的。
应如晦懂得江桓的意兴阑珊,他给他添了一杯酒,“文人附庸风雅,有时候也不过是被境遇所迫,你若是不感兴趣,也不必强求。”
“我这不是……”江桓嘴里卡着话,他肯定不想承认自己为了想跟应如晦多说些话特意去学了什么,于是就把自己手里的酒一饮而尽,避开目光去看了看月亮。
一阵微风拂过,庭院里的树簌簌响动了一阵,两个练武之人仿佛忽然有了什么预感,同时把酒杯放下了。
“你也觉得……”江桓对视了应如晦一眼,缓缓把手放到了一旁的刀把上。
视线缓慢地扫过周围,灯笼光照到的地方无甚动静,接着在一棵暗处的树后,响起了一声:“是我。”
这声音应如晦先认出来了,他惊讶之余去按住了江桓的手,然后看到那棵树后,走出了一个人影。
灯笼光洒下,暗色的衣物与黑暗融得几乎没有差别,但他一张脸太过别致,让人实在不可忽视。
“见鬼。”江桓心里先骂了一句,“他怎么来了。”
应如晦藏起脸上的惊讶,起身去迎了几步,“白将军怎么会来?”
白烬从阴影里走到灯火下,他看清了是应如晦与江桓在喝酒,但他往后多看了几眼,也没找到第三个人的影子,“孟凛呢?”
白烬有些生硬地发问:“我方才去他的院子,并未找到他。”
白烬本不该用这样的语气,他赶了一天路,直接去了孟凛的院子,但他不仅没在院子里找到孟凛,没找到吴常,连带跟着孟凛的陈玄与其他暗卫,都不在院子里。
那屋子并未锁住,白烬推开房门,走到孟凛时常坐的书案旁边,他从桌上摸到了一层薄薄的灰,这屋子里收拾齐整,竟然不像是有人常住的样子。
白烬的心竟然开始狂跳,不好的预感占据他的思绪,他直接来找了江桓和应如晦。
江桓的第一反应就是替孟凛遮掩,“他,他出去了,这些日子暂且不在府里,不是,你不是回北朝了吗?现在怎么回来了?”
白烬语气染了一丝着急,“那他去了哪里,何时回来?”
江桓不耐心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他……”
应如晦拉住了江桓,他朝他摇了摇头,应如晦向白烬走了几步,“我与白将军同朝为官,知晓你的为人秉性,因而也不想欺瞒于你。”
“孟公子他……去了南朝。”
“什么?”白烬心里仿佛忽然响过一声惊雷,他设想过的所有可能里面都没有这一条,他竟然不可置信地又问了一句,“你说什么?”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江桓叹了口气,“你跟我过来,孟凛他给你留了一封信。”
江桓依照孟凛的话给白烬寄了第一封信过去,他实在没有想到,这才一个月不到,这事就这么挑开了,白烬怎么会现在回来?
江桓见白烬好像木然地站在原地,他又补了一句:“孟凛说你看了就都明白了。”
江桓去自己卧房把锁好的信拿了出来,他犹豫了一会儿才交到白烬的手里,“这都是孟凛的意思,不管里面写了什么,你可别拿我来出气。”
江桓推了推应如晦,这场景他实在不想多留,他代入其中想了会儿,自己指不定还得接受不了。
人都走了,白烬一个人站在屋子里,烛火下的身影仿佛有些落寞似的。
手里的信一时仿佛有了千钧的重量,白烬看江桓方才的反应,忽然有些望而却步了,复杂的情绪一时郁积于心,在他毫无准备的时候,忽然攻得他措手不及。
白烬其实是有些生气的,有什么事情,孟凛能让江桓和应如晦知道,却要瞒着自己,他明明早先答应了自己不会不告而别,可他怎么会去了南朝,而在最近的信里对自己只字不提呢?
但白烬是相信孟凛的,若非出了什么大事,他应该是不会做出这样事情,可又是有什么事情,逼得他……
罢了,白烬不想再往下想了,他把信拆了开来。
“多日不见,吾心难安,见字如面,聊表歉意。”
孟凛知道自己不告而别,心里其实积了许多愧疚,他其后三言两语说清了白烬走后发生的事情,孟明枢传话要让孟凛回南朝,孟凛未曾理会,但孟明枢并不死心,那日孟凛与吴常出行,他派人当着孟凛的面杀了吴常,由此逼迫孟凛回去。
常叔对孟凛来说已是亲人,从前因为吴常孟凛不曾动回南朝的心思,可如今吴常被孟明枢以惨烈的方式杀了,孟凛不可能不回南朝替他报仇。
孟凛终究是要直面自己的身份的,他与孟明枢的关系一日不曾磨灭,只要孟明枢对他发难,他一日都得在其中煎熬,唯有主动出击,哪怕前方艰险,他亦然想要一试。
唯独他放不下白烬。
“此事不曾告知,乃是因为不想让你烦忧,即便你因此责怪,我亦不忍让你腹背受敌,此事乃是我心有私念,来日无论如何责怪,我也不悔当初决定。”
傻瓜……写于纸上的一言一语仿佛忽然变成细碎的尖针,从白烬心里一根根扎了进去,他无处闪躲,只觉得心里疼得难以名言。
白烬也不知道自己心里是心疼还是难过,亦或是生气?这时候他其实没有立场与孟凛再生气了,哪怕他是不告而别,但他不告诉自己也是因为念着自己的情绪,就像世间有亲人逝去,家中的子女尚且为要事烦忧,就有长者不愿让他因此伤心不已,耽误了紧要之事,就算是逝者,也不想让自己的离去,牵扯到生者的来日。
白烬心乱如麻,他甚至顾念不了孟凛瞒他了,他心疼孟凛当时的处境,亲眼看着亲人逝去,他当时是忍受了如何的煎熬,才终于提起笔来,写下书信然后一个人离开?
况且南朝危险莫测,如今一个人远在南朝的孟凛,又是有什么样的人生际遇?
白烬翻开后面的纸页,继续往下看着:“此去南朝,心中所想本是满心怨恨,可前后思量,不免自问,这世间芸芸众生,皆是只为了自己的悲喜哀怨而活吗?”
“我出生之时正逢战乱,我亦出生于南都长乐,年幼多年皆是生长于南朝,若非孟明枢弃我不顾,如今按其发展,我怕是与现在立场有异,辗转南北,又立于岭中,其实这世间的朝堂纷扰,胜败之名,我从不曾在乎过。”
“直至与你相识,白家出身将门,世代忠骨,哪怕遭奸人所害,亦不见你有过异心,出入朝堂一心为忠,此等赤诚我百世难修,见你如此,其实我曾为你不平,这世道本不该值得你如此尽力而为,但一遭生死来过,我又忽而另有思量,情愿以己之身,或许可以一试,可否成全你两世不曾变过的救世之心。”
“爱屋及乌也好,此去南朝,若能成全你的一腔赤诚,我也定当竭力以赴。”
“——初寒手书于夜。”
夜里的烛火不过指甲大小,且于风中左右摇摆不定,不过些微大的清风,就可留下独独一缕青烟,但暗夜之中,一盏烛火足以照亮方寸,指引着前方的道路。
白烬将那封信小心翼翼地折叠起来,他放在手心看了一会儿,把那封信揣进怀里,放在了心口的位置。
白烬把目光挪向窗外,面对着南朝的方向。
他忽而比什么时候都想孟凛,他想去见他一面。
作话:
下一章就干柴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