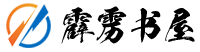白烬沉下眼看那太医,“太医如常诊治便是。”
一边受着诊治,白烬一一见过了淮北的几位官员,等到寒暄终了,那太医也诊治完了。
太医跪地挪动着身子向太子行礼,“回禀殿下,白将军脉象虚浮,的确是风寒之兆。”
“风寒之兆……”齐恂眉间一皱,那表情似是在为白烬担忧,他这才往前走动几步,“听太医说,从前太医院问诊的簿子上,还未曾有过几次白将军的名字,你为我朝呕心沥血,从前以为你是铁打的身躯,如今竟也病来如山倒,还望着白将军早些好起来才是。”
白烬一直很是奇怪,这世间人的虚情假意竟也能做得真情实感一般,齐恂竟然亲自上前来替他掖了下被子,若他方才被太医诊出了疫病,隐而不报,他此刻怕是避之不及地要降他的罪了。
白烬面无表情的垂下首:“多谢殿下。”
齐恂又瞥了一眼那太医,示意他起来回话,“白将军可还有旁的征兆?”
这太医今日奉命来给白将军诊治,他从前听过宫里的风言风语,大半年前青山猎场那事传得很大,在那里头没什么别的伤亡,只死了个入翰林院不久的新科状元,本来事情过去大半年了,太子殿下所罚之期也已经过去,但当初那个葬身青山的状元郎好似是有个至交好友,正是如今圣眷正隆的白将军。
孟大人一死,他俩从前没太多人说道的交情一时许多人都知道了,京城里还传出了他俩少为同里,长为同僚的美名,但当初青山那事归咎之处,怕是还要牵扯到太子殿下,因而许多人觉得,白将军和太子殿下怕是有些不大对付。
朝廷里的明枪暗箭太多,齐恂提前告知他一句“只管如实说便是”,就能引得这不好做的太医心里思量千遍,他谨慎道:“白将军舟车劳顿,有些太过劳碌之相,添上早几日风寒侵体,这才染了风寒,若下官没有猜错,将军今日早上怕是还吐过一回,有些胃口不佳难以入食的征兆。”
白烬好像是惊诧太医看得准,“太医所言正是。”
齐恂没听到想听的,脸上竟也还挂得住,他朝营帐里扫了好几眼,叹了口气,“白将军病得如此重,还要委屈你住在此处,如今哪怕是再马车劳顿一番,也不忍心再让将军受这等苦楚了。”
“你觉得可有道理?”齐恂回过头去,“薛大人?”
淮北巡抚薛允赶忙接过话去,“殿下所言正是,下官其实早就预备了府上厢房,只待白将军移步而入。”
“薛大人盛情。”白烬平静地朝他点了个头,“白烬自然不应当推辞。”
“既然如此。”齐恂负手转过身去,“那我等就不打扰白将军休息了。”
等到一伙人鱼贯而出,杵在一旁的楼远才快步到白烬的身边,他欲言又止:“将军……”
白烬示意他暂且等等,又忍不住咳了几声,那惨淡的面色一点也不像假的。
“将军您这是……”楼远放低了声音,“真的病了?”
白烬朝他摇了摇头,却又顺了顺有些难受的胸口,他想了昨日离开南朝的场面——
孟凛刚写完了方子,他吹了吹上面的墨迹,“听你方才所言,齐恂是想让你染上疫病,却不想阴差阳错,这罪让林归受了,所以你借口染了风寒,一面掩人耳目,一面让他真以为你是得了疫病,唔,让我想想……”
白烬将墨放下,敛眉道:“你是怕他带人过来,验我的病症?”
“要我我就如此。”孟凛将药方折好了递出去,“要是能刺杀了你一劳永逸,但若是失手了,就带着人过去看你的病症,你若是染了疫病,那就是隐而不报,拖累全军的大事,但你若是没有染病,那就是欺瞒于上,除非你真的病了,那才让人没话来说。”
“可惜了。”孟凛上下打量白烬几眼,笑道:“我家将军太过生猛,实在是甚少生病。”
白烬迎着他的目光,“你这像是不安好心。”
“这就不安好心了?”孟凛摇摇头,“那我的坏心眼你还是见得少了。”眼珊亭
“不过此番我倒是好生感动,白将军竟是为了见我而撒了这么大的谎言。”孟凛看着白烬时用手去勾他的腰带,被他的手攥着拦住了,“但我料想你这次回去,若是要让你在齐恂面前装出一副病恹恹的模样,怕是有些为难你。”
孟凛勾唇道:“白小公子不妨现在学学我平日里是如何柔弱的?”
白烬一怔,他似乎是想了一会儿,摆头道:“不学。”
“你体弱多病我心中怜惜,只盼着你早日康健,怎能拿来玩笑一般。”白烬认真地对着孟凛的笑脸,“见你如今泰然处之,我心里更是难过。”
孟凛不禁有些发愣,他被白烬捏了捏手,这些年伤病过来,仿佛只有白烬还觉得,他会有康复的那一天吗?
孟凛呆愣了一会儿就偏过了头去,胡乱地另外起了头,“那我这里还有,还有一个法子,就是可能要你吃点苦了。”
孟凛从白烬手里把手缩回来了,他打开书桌上的一个抽屉,从里面取出了一个小小的药瓶,他从药瓶中倒出几粒药来,但那几粒药的颜色都不一样,孟凛还凑近去分辨了会儿。
白烬一晒:“你葫芦里都卖的些什么药?”
孟凛挑了一粒暗红色的药丸,他玩笑道:“我药罐子里全是不安好心,可惜今日也要给白将军尝尝。”
“风寒之兆也是从脉象里看来的,这药吃了就能让你病上一病,但我实话实说,生病的滋味,其实并不好受。”想到这里,孟凛递出去又犹豫了,“是药三分毒,小公子,我有些舍不得你……算了……”
孟凛正要把药收回去,却被白烬一把拿去,“吃了这药,我听你的好生将养。”
“可是……”孟凛垂头丧气一样,“我忽然想起从前,应如晦让你去涉险当了诱饵,我心中很是心疼,因而还教训了应如晦一回,可如今我给你这药,那我自己也岂不是……”
“你也说了齐恂生性多疑。”白烬站在一旁,宽慰似的去摸了下坐在桌前孟凛的头,“为免他起疑,如此也算良计。”
……
可白烬没想到这药吃了当真这么难受。
白烬在黎明破晓前赶回了淮北,他刚进营帐,两把长刀立即横到他的身前,差点就割了他的喉颈,他那连夜赶路的疲惫全被一根绷紧的弦给除去,如此如临大敌的阵仗,白烬觉得自己怕是有些对不住楼远了。
楼远对着白烬一口气松得比上回还要夸张,“将军,您可终于回来了。”
“您要再不回来,属下就只能给您磕一个了。”
“将军可再别做这种惊心动魄的事了,您就当属下是个鹌鹑,我胆子小着呢……”
白烬心里虽有歉意,却忽然觉得楼远和他那个话多的哥哥似乎还是同出一脉的,只是平日里那血脉没能觉醒得如此明显。
而等到天刚亮的时候,白烬就收到了个偷偷送来的纸条,“太子即刻到访。”
——是从前祁阳的县令,如今的淮北通判张全送来的。
“这意图也太过明显了!”楼远愤愤不平,“昨日才刚叫人刺杀,今日就来探视,这不安好心得如此明显,他怎么能如此对你?”
白烬眉目在屋里的烛火下冷意十足,“我与他的恩怨,还不止这些……”
然后白烬将孟凛给他的药服下了。
结果白烬当即就将肚子里本就不多的东西吐了分明,一丝丝的冷意爬上了身,仿佛有什么吸走了他的力气,忽然而来的睡意与一路的劳累在他心头折腾,白烬让人小心把林归挪走之后,撑不住地睡了过去。
他昏沉时还想,孟凛平日生病,都这般难受吗?
后来白烬敏锐地被外面的动静吵醒,就是齐恂带着人过来。
他等齐恂走远了,才示意楼远不必再憋着。
楼远还是关心地摸了下白烬的额头,“将军,属下本以为你是装的,还感叹了你的演技高超,但你这是真的病了啊,你这一趟是去了何方?怎的弄成这个模样?”
“我……”白烬摆了摆手,“我没事,这些日子劳烦了你了。”
楼远又一脸的苦笑,“旁的不说,将军这句话是不假的。”
等到日头高了,接送白烬入城的马车终于驶进了城门,白烬即便难受,却并未闲着,他听楼远说了这些日子城中的情况——一场雨后放了晴,气温回升了不少,加上把病患挪去了城外,再染病的人少了许多,太医那边是林净山担了重担,他几乎日夜不眠地研制汤药,如今虽然并未成功,但是已经帮人缓解了许多症状。
白烬要撑不住睡着的时候跟楼远说了一声,让他两个时辰之后喊他起来,他要亲自去见一趟林净山。
而在城外远处,一辆马车又背离着淮北城远了,太子齐恂并未告知众人,只带着手下几个人,往祁阳县城的方向去了。
他说要去拜祭一番秦老将军。
马车驶在石子路上有些颠簸,齐恂似是闭目养神,今日没能抓到白烬的辫子,他其实心中有些不悦,他听着谢化在旁边禀告:“白烬他们收拾入城的时候属下去查看了,今日不知是白烬使了什么阴谋,竟然得到太医诊断,但是实际上,属下观察到他身边那个下人,好像叫林归,他也昏迷不醒,殿下去之前,那人就被挪去了别的地方。”
齐恂极浅地睁了下眼,“如此就说得通了,得了疫病的是林归,那日你看见屋里的人也是林归,但你觉得那个拿刀的,是白烬吗?”
谢化摇头,“两三招虽然试不出深浅,但是属下肯定,那人不是白烬。”
“不是白烬……”齐恂睁眼来问:“那我们白将军,又去了何方?”
谢化不知如何作答,只低着头。
“这淮北可是他的故土,他可去的地方多了。”齐恂撩开马车帘子看了眼外头的树色,“从前只觉得白烬长得周正,他平日里不受伤不生病的,带了英气,但今日他病了面色惨淡,柔和了许多,我忽然觉得……”
齐恂的手将窗帘放下,眼里闪过一丝锋芒:“他生得有些眼熟。”
“他既是生长于祁阳,我有些疑惑,倒想去探究一番。”
作话:
“白烬长得更像他的母亲”